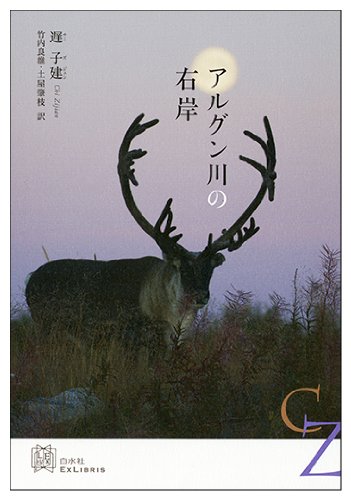血泊中的少年——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有感
有论者提到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区别点在于前者是纯主观的感性批判而后者则是经由理性思考总结之后所形成的一种见解,这在我看来是极为正确的。虽然从一部作品的整体定位讲,普通个人的所有主观好恶对于其历史评价的形成而言是无关宏旨的,但是笔者仍旧认为,作为文学批评之前的一个环节,读者投入感情的理解实际上并不非毫无可取之处,经由一个文学文本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是我们将自身投射到文本之中所得出的最为真实的反映,而这反映对于所有的阅读者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也无人能够预设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碰撞究竟会发生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而生成何种不可预估的结果,《少年维特之烦恼》(后称《维特》)恰恰是能够造就这种情况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一
后世的论者在谈到这部伟大的作品之时通常持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强调小说本身的阶级性与革命性色彩,认为它是一部革命作品;而另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则认为它是一部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自叙传色彩的爱情悲剧。在笔者看来,其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一方面,从作品的内容而言,绝大多数篇幅被用来刻画因绿蒂与维特之间的情感纠葛而产生的他个人的心理变动情况,即便是在绿蒂缺席的篇目里,她也仍旧潜藏在维特的思维与行动的身后,而并非真正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正如歌德自己所言,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自身“巨幅自白的一个片断”,维特的故事也不例外,它实际上是歌德将自己同一个友人的经历糅合之后创作出来的结晶;除此之外,作为代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最高成就的作品,《维特》本身就带有典型的“狂飙精神”以及鲜明的主情主义色彩,尽管这部作品更为主要的内容是对维特个人因为爱情而产生的心理变化的描写,但在这种表层的爱情与情感演变之下,我们也不难发觉其中或多或少地带入了某些革命精神(主要从维特在城里所受到的打击体现出来)。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更应当被看作是一部具有些许激进革命色彩和自叙传色彩的爱情悲剧。
而造成上述悲剧的直接原因,在笔者看来,实际上还是缘于少年自身的性格。一种由于极度敏感而时常处于激烈变动状态的情绪化以及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理想主义心理共同构建起维特人格的主要方面,他曾在信中提到:“你肯定没见过哪颗心像我这颗心这样反复无常、捉摸不定。亲爱的,难道还用得着我说,常见我忽忧忽喜,从甜蜜的感伤忽然转为疯狂的激情,你多么替我担忧么?我也把这颗心视为一个病儿,随它任性而行。”[1]6他是任性的,恰若一个年幼的孩童,他也承认“人世间唯有孩子们最贴近我的心”[1]28;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他会为了庭院中将到寿限的树木而伤心落泪[1]93,也会在一场简短的讨论中突然联想到悲伤的往事而大动感情[1]33;他的心绪时常变动,甚至一天之中多次提笔写下自己难以平复下来的感受(例如1771年8月8日、1772年10月27日的信件);并且更为致命的是他对情感的态度:他不仅对爱情充满了赤诚的热情,强调感性与情感的决定作用,指斥理性的过度拘束,认为它是阻碍“天才的激流”奔腾澎湃、掀起巨潮的堤堰和渠沟,而且保留着与生俱来的执拗。上述这些性格在维特的身上汇聚,最终成为他在主观上感到自己同现实世界与感官世界都有些格格不入的直接缘由,他说:“当我目睹人类的创造和研究能力受到限制,当我亲见人们进行活动无不出自私欲,而这些欲望仅是延长我们可怜的生命,并没有任何目标之时;随后呢,我又发现一切试图从探索理想目标以获得慰藉的行动都是枉然,就好比一个被囚禁的人在狱墙上描绘种种色彩缤纷的形象和光辉夺目的景色……我返回到自身以发现另一个世界!这里也同样满是预感和模糊的渴望,却缺乏创造力与勃勃生气。”[1]10在笔者看来,这种不合时宜的背后显露出维特的内在精神思想同整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之间所产生的巨大割裂(即个性与社会的对立),如果说在此处仅仅是通过维特的心理独白告知我们这种割裂的现实,那么他同阿尔贝特有关自杀问题的争论以及后来的主动请辞都不约而同地为这种先在的自白提供了实际的证据。如果将维特的悲剧看作是由一颗威力巨大的炸药所引起的,那么个性与社会的对立则是隐匿于包装之下的不为人所见的火药,维特的性格是引燃炸药的火光,他的那份执拗即是那根短短的导火索:尽管他的性格之中不乏让他感觉自己“随时都能够离开他的牢笼”的随性的一面,但是当他面对爱情的时候,执拗却又远远超出随性从而使他认准了绿蒂而不愿放手,即便他所渴望的一切已经不可能实现,他仍旧宁愿从缥缈的幻影中获得些温情来温暖自己而不愿去选择其它的出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维特的悲剧性结局其实是性格与时代所共同造就的。在《编者致读者书》中“作者”对维特的悲剧进行了阐释,“他觉得一切的一切都迫使他无所作为,所有的出路都堵塞不通,而他也学不会普通人庸庸碌碌打发日常生活的能力。于是他最终还是完全顺从了自己那种惊人的感情、思想和无限狂热,永恒一心一意悲惨地和那位温柔可爱的女子相周旋,毫无目的,毫无希望,既妨碍了她的安静,又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日复一日地接近着一个悲惨的结局。”[1]115现实中接二连三的打击以及社会的凡庸使他对整个现实生活失去了信心并感到深深的绝望,而情感的受挫经由他个人性格的放大也使得他愈发孤寂地沉沦于无尽的伤悲之中,但当面临被迫合乎社会“绳墨”的规约与主动沉浸于无结果的情感这二者之间的选择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现实确实可以被看作是造成少年最终亡逝的更深层原因,诸多论者所言及的“革命性色彩”在这里大概便能够得到隐性的体现。
二
如果说维特个人的性格是造成其走向悲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他心理状况的变动历程则作为一条线索将他走向毁灭的过程以一种极为清晰的方式串联了起来,纵观整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维特的心绪是在不断地向恶化的情况发展,而引起这种变动的情节发展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前推进。
总体来看,维特的心理状况演进历程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771年5月4日至7月30日,初至乡下所达到的内心和谐以及初逢绿蒂时所感到的短暂幸福。
刚刚从城市回到乡下的维特在自然美景之中流连忘返从而达到了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心境,在这种身心愉悦的状态下,当他在偶然中见到绿蒂,便自然而然地被她所俘获。面对近乎完美的绿蒂,他完全地陷入了毫无前景的单恋之中,尽管从一开始便知道这终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旅程,但是他却觉得“我心满意足,正在品味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幸福……不管我今后的命运如何,我可不能再说,我从没有享受过欢乐,生命最纯洁的欢乐。”[1]26这样的话语,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出着一种不负此生的无憾,而且也同时显露出他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而无法自拔的心态,从这一点来看,在一开始维特就是以一种倾其所有的态度去追求绿蒂的。从七月十三日开始短暂的半个月光景,维特完全沉浸在对绿蒂的爱恋之中,“从此以后,太阳、月亮、星星都静静地照常运转,我却不再知道何谓白天,何谓黑夜,我周围的世界全部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每日每夜每分每秒无论清醒还是沉眠,他的脑海中只有绿蒂,那个时候的维特就像是一簇愈燃愈旺的蜡烛,他在发出灼热的光芒的同时也在更加快速地走向灭亡。
1771年7月30日至9月10日,由欢欣的巅峰陡转至低谷,维特逐渐陷入疑虑与痛苦。
幸福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随着阿尔贝特的归来,他所散发出的火光迅速地减弱,从这一阶段的书信之中我们不难看出矛盾与痛苦迅速在他的体内滋生,他自白道:“我偶尔也有精神振奋的瞬间,但是——只要我知道该往何处去,我早就走了。” 他无法听从威廉的建议,因为深陷爱情之中的人总是难以摆脱对于渐趋幻灭但仍旧存留些许温存的期望,在维特看来,他对绿蒂的爱恋已经成为维持自己不陷入绝望泥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对自己的处境始终看得十分清楚,然而行动却像一个孩子……没有悔改的迹象。”[1]45尽管这份爱恋的结果就那样决绝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并且他也知悉一切都不会按照他的期待进行,但是由于内心无法抑制的爱意,即便充满了矛盾他还是不愿放弃。歌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透过对于维特这样心理的细腻分析从而揭示出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却难以用语言说清的事实,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维特》之所以直到如今还被世人津津乐道地捧读的原因之一。
1771年10月20日至1772年7月29日,出走寻求排遣但并未成功,最终更加悲伤地回到绿蒂的身边。
维特最终还是下定决心离开绿蒂,他试图摆脱这份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恋所带来的无尽的苦恼,所以选择进入城市,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一切并未顺遂他的心愿。进城后的维特发现自己依旧无法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无法适应“使人难堪的市民社会关系”,这从他不断地抱怨和愤慨之语可以看出。他只求人们让他走自己的路,但是这简简单单的希求竟难以实现,而当他再一次陷入困境,他发现自己所想的人仍旧是绿蒂,尽管两人此时相距甚远,但他却难以摆脱对她的思念,城市的压抑生活让他在心中痛苦地自白:“我丧失了使我富于生命活力的酵母;那种让我精神饱满直至深夜的兴奋剂失踪了,那种让我从清晨的睡梦中觉醒的诱惑力消逝了。”[1]73他试图将自己的感情转移到贵族小姐B身上,但我们能够发现他却还是在下意识地将二人进行对比,还是在对小姐B讲述自己心心念念的绿蒂的一切。他失败了,这在他被上层人士从他们的聚会中驱逐出来的时候得到了正式地宣告,他的天性使他难以介入市民关系这一张硕大无朋的巨网之中,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压抑以及内心对于绿蒂情谊的不断复苏,他第一次明确地想到选择死亡:“我真想切开一根血管是自己获得永恒的自由。”[1]79在此之后,自杀的想法便不断地出现在他的信件之中,面对无可挽回的结局,他才发现自己在思想和现实中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还是只能够回到乡下,他的出走本是想要找寻新的开始,然而命运却最终阴差阳错地让他带回了新的悲伤。(“如今我从遥远的世界归来了——噢,我的朋友,带回家的只是无数破灭的希望,无数失败的计划!”[1]82)
1772年8月4日至12月20日,几经思虑之后陷入对毫无可能的爱情的深深绝望,最终下定决心走向死亡。
再次回乡的心境早已不复从前,一方面,在面对曾经的景致之时他“觉得自己颇像一个回到城堡来的君主的幽灵,当年他在鼎盛时期修建了这座宫殿,装潢布置得极尽豪华之能事,临终时满怀希望地遗传给了心爱的儿子,而眼前却是一片烧毁殆尽的废墟。”[1]88这样的心绪表露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预示着他的悲惨结局;另一方面,他对待阿尔贝特的态度进一步趋向恶化。早在此前他就已经表达出对于阿尔贝特的不满,而到了1772年9月3日,他竟开始期待阿尔贝特的离世,这一切的白日梦以及其背后所显露出的企图让他觉得自己的卑鄙,并且也预示着此次回来他同阿尔贝特之间关系的全线崩盘。这一时期,在他眼中,阿尔贝特是四平八稳、无趣且单调、缺乏敏感心理并且在得到绿蒂之后显露出了“餍足和冷漠”,这些正同他自己身上的充满热情、极度感性形成了对照,因而他从自身的情况出发,下意识地认为绿蒂所爱的或说更适合绿蒂的应当是自己而并非平庸的阿尔贝特;而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其他人,则会发现在众人眼中的阿尔贝特实际上是可亲可敬并且十分照顾维特的感受的,一反维特眼中的状况。这在某种层面上体现出维特将自身所具有的某种偏见投射到了“情敌”阿尔贝特身上,而他本人实际上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只不过爱情的盲目让他无法抛却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对自己说了又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这又有什么用呢,我的内脏都给撕碎了。我永远学不会合乎时宜。”[1]115
除此之外,在现实不断地冲击下,此前他对于绿蒂爱情的期待与希望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并且他竟认为这种痛苦只有消除自己才能够得到解除:“我确实感觉一切过错全在我自己……正如当年一切幸福的源泉全存在于自身,今日痛苦的源泉也出于自身。”[1]99这种深深地无力感在他又一次谈及死亡时展露无遗:他开始觉得“一个人的存在并无多大价值,简直很少价值。”由此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虚无的认为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转变更进一步地引导着他走入消沉,这种消极的认知同对自我的否认(即认为只有自己死去才能消解痛苦)相结合,最终沾染上“我是为了绿蒂的幸福而自杀”这种错误的想法,他才会在信件中写到自杀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并且从容地死去。但是尽管已经考虑好这些,他也仍旧会感到痛苦,减轻痛苦的方法其实极为简单,然而他自始至终都对之视若无睹,在这种情况下他徒然地感到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无能为力,所以才会愁苦地述说:“你完全不知道,你的不幸存在于自己破碎的心,存在于错乱的头脑,世界上任何君王都帮不了你的忙呀!”(P106)受伤的心灵无法得到救助,他渐渐地沉入绝望的深渊,唯有死亡才能让他解脱,他祈求上帝让他短暂的一生结束,让他能够回到幸福的境界,但等来的仍然是沉默无语,所以在最后他选择自己做自己的行刑人,并将自己拒斥在“世俗的天国”之外。
众所周知,爱情本身是针对双方而言的,当维特自认为一切都再无希望的时候,绿蒂此时的所作所为无疑也加速了少年走向死亡的进程。她告诉维特“去找吧,寻找一个值得你爱的姑娘,然后回来和我们团聚,让我们一起品尝真正友谊的幸福。”[1]121从她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她不愿就此让维特永远离开自己,因为不仅“他已经在她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在她心里所不愿明言的是“她确实暗暗衷心希望把他留给自己”,这些都说明她对维特存有强烈的感情;但另一方面,她又囿于世俗社会的观念而不能够勇敢地突破它们的重重束缚,所有的矛盾涌上心头,“她的思绪又再三回到维特身上,她已失去他,却又不能舍弃他,而又必得丢弃他!还想到维特一旦失去了她,就等于什么也没有了。”[1]138几经周折,她最终选择了这个看似稳妥但实际上是将维特推向了最后的死亡的一个方法,这无异于是亲自向维特宣告了他自己空想的恋情的消亡,也由此将他推到了无尽的深渊之中。
诸多论者所持有的革命作品观点大抵是由此处以及此前的城中经历所引发出的,在笔者看来这并无不妥,但无论是对于贵族阶层的迂腐守旧还是对封建社会观念的抨击都是潜伏在小说的表层之下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维特与绿蒂之间的爱情悲剧还是维特遭到贵族阶级欺侮的事项实际上都反映出歌德在爱情与人物心理之外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更为深刻的反思。
最后的阶段,为死亡点缀华美的羽翼。维特之死的悲剧性之所以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高度,这末尾的升华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点。如果说此前维特对死亡的向往是源于现实的不容挽回以及个人性格的缺陷影响下的被迫之行,那么在最终同绿蒂的见面之后则戴上了一层更为“高尚”的献身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言:“绿蒂呀,我但愿能够享有为你而死、为你献身的幸福!我乐意勇敢而愉快地死去,只要能够给你带来安宁,使你的生活恢复往日的欢乐。”[1]他的心绪正是在这种转变之中得到了平复。
三
现在的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作品的形式足以决定作品所要含括的内容,在笔者看来,《维特》的形式与内容之间,一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联——即二者的互相选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逻辑合理状况下的对于传统形式的打破与创新。
歌德意欲通过表现一个青年的爱情悲剧来表达更为深刻的思想观念(它或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批判,或是对于返归自然等精神气质的宣扬),而这种所要表现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同书信体这种特殊的形式相契合,与此同时,书信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私密性因而更容易混入写信人平时极难为外人所知悉的个人情感,在这种特性的指引下,小说的形式与内容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互相选择的关系,依据这种关系建构起来的《维特》也由此被贴上了“主情主义”的标签;此外,它的背后亦包含着写信人的一种极度的渴望得到理解读信者的理解的心理预期。
小说的具体内容对上述这两点体现得十分到位:从写信、收信的双方来看,维特和威廉二人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好友,在这种关系下他们之间无所不言,尽管我们只能看到维特所写的信件,但是从他书写的口吻以及其中的内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威廉实际上在不断地为维特提供自己对于他所遇到的问题的看法与意见,并且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也一直在开导他,在这种情况下,维特才能够不断地书写信件,从而使得一切都能够顺理成章地继续发展下去。除此之外,书信体形式亦为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在合理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效果提供了可能:不同时间节点所写下的信件能够揭示出维特当时的心理状况,例如有的时候两封信之间仅仅相隔一天甚至是更短,而有的时候则相距半个多月,这些不同的时间间断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为人物心绪的变动勾勒出了一条可追溯的线索,并且间隔时间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处于未知的状态也能促引起读者的思考与遐想。
任何一位闻名于世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学家所必备的特质之一即是创新意识,歌德也不例外,这种意识在《维特》中就已经展露出来,它在形式上主要体现在临近末尾处的《编者致读者书》。在笔者看来,这种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安排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之中得到了一种特殊的感受——叙述视角的转化以及写作方法的变动带来的新意。一方面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局外人的视角,尽管“作者”在情感态度上亦是同情维特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改变了第一人称叙述的纯主观性;另一方面“编者”的身份本身也具有某种引导作用,这不仅使我们得以跳出维特、绿蒂、阿尔贝特三人所构成的狭小圈子,站在一个更加合理的视野下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读者在此前阅读中形成的对于三位人物的看法进行纠偏;而且为书信之外的材料介入文本提供了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者”向我们展现了维特自杀前后的种种情况,从而让我们对整个事件能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仅就这两点而言,这种在因循之中的创新就足以被视为成功。
参考文献:
[1](德)歌德著,张佩芬译,《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2](匈)卢卡契,申文林译,《论<少年维特之烦恼>》,《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
[3]王诺,《<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心理分析》,《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jpg)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