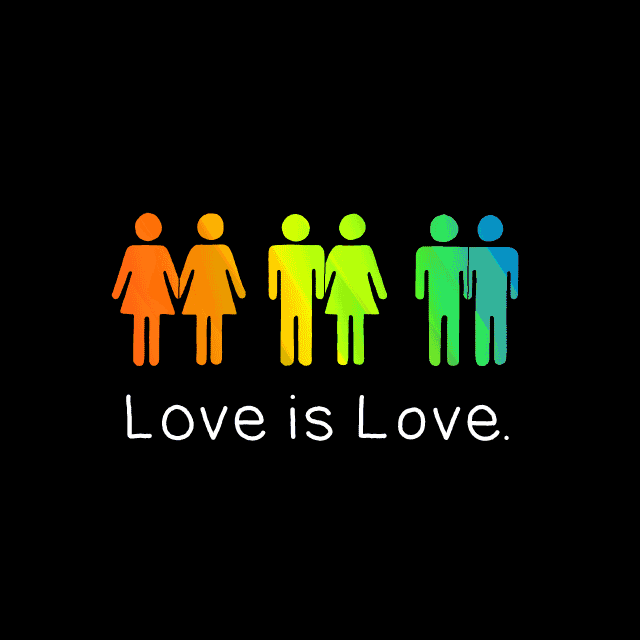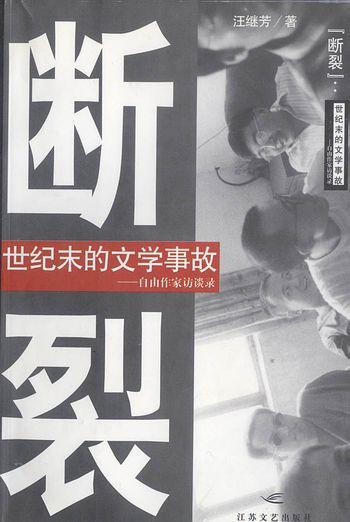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人有病天知否》读后:历史并非无言,也总有人会记得
当代文学史料,少做判断,通过连缀材料来呈现态度,胜在材料的充实和丰沛,与对历史人物所处情境的体贴。但在组织架构和历史研判的方面不如钱老和洪老的敢下结论,尖锐度也稍欠一些。倒是让人颇有些惋惜,因为掌握的材料是这样的丰富。期待口述原稿重见天日的那天。
阅读中全然是感慨和惋惜,止不住连声感叹。人们在这张权力的赌桌前站定投注,玩到最后没有一个赢家。“革命”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一台既已开启就无法停下的巨大的绞肉机,任何人卷进去都将万劫不复。甚至高层也是如此。因而向外示人的只有斗争的残酷与严苛。
大致说来,笔触所及人物可以分四组:
时代的边缘人物:俞平伯、沈从文
风云际会者:老舍、丁玲、郭小川
被抛出的时代写手:赵树理、浩然、汪曾祺
补笔:严文井、林希翎
边缘人物的落寞其实多如沈从文那样,更多是在心理上感到与群的相隔与受到整治的恐惧忌怖,但他们也因此能更早地抽身——尽管是被迫甩出的。从一个较为乐观的方面看,相较于弄潮儿的沉浮升降,他们长期处在被否定和无可翻身的位置,反倒是给了自己更早释然的机会。
一如沈从文在面对文革的时候已然不复建国前期那样沉痛以至于想到自毁,反而是在文物研究难以为继的时刻主动开辟新的领域,做起旧诗来。
俞平伯也与沈从文相似,作为建国后第一批被抛出批判的对象早早靠了边,却还是不愿放弃,继续做着该做的事情,兢兢业业的。
张新颖写沈从文在没落中与友人的相会,在被抛掷的情境中是令人觉得无比温暖的。在批判俞氏的会议上也是金岳霖试着回护了一番。可见,这些“老人”虽然自己身陷囹圄,却还是在沉痛中带着悲哀,努力过活着。并将美好留给他人,将痛苦留给自己。其背影到确实令人难以忘怀。
说到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过后,留在更多人心中的其实都还是那些酷烈之中偶有流露的温情,是那些人心与人心的相贴:丁玲记得的是刘白羽在自己被批倒后骑车前来谈心,郭小川对艾青的允诺,黄秋耘与陈翔鹤在低沉处境中的相遇相知(但令人难过的是,才了解到陈翔鹤当时批判俞平伯时也是激愤异常凛然刻薄,可见人被其所处环境异化的剧烈程度)。
身处风云际会之中的干部则全然不同,自己今昔处境之对比已然是触目惊心,更别提一次又一次献忠而又被谤,理想与热情一次次点燃又被浇灭,到最后还有一种放不下却又难以再信的幻灭。此种冲击实在是难为外人所体会。
老舍、丁玲、郭小川或许代表了三类对新社会有着殷切期待且在一时间融入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党外、党内出局者、党内有权势者。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陷入到越是热望就越是失望的悲剧性循环之中。
对于老舍而言,建国后的经历到他离世的那段时间就像是一场又一场串联起来的大梦,而他陷在里面,不愿苏醒,但越是这样,梦醒时分就越悲哀,因为发觉现实完全不是梦中想的那样。巨大的落差让他难以忍受。在另一个角度看,他此前的一切举动虽然不可否认地带有自主歌颂的色彩,但又有谁能否认其中不存在因震动而被裹挟着向前和自保的意味呢?
陈先生提到了老舍在被抛出之后的一个细节:“有一次市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现在读来真的是声声泣血,垂死者渴求岸边芦草却仍被视而不见的那种感觉令人难过。
而老舍修改《春华秋实》的经历则细致地展现了一个作家是如何将自己融于群而消解掉作品中最不能消解的自我的过程的(笔者将其称为建国后创作的“去个体实际经历化”,也就是陈晓明所谓的“写作主体主动或被迫地把自己从以往血肉相连的历史中剥离出来,进入另一种陌生的突然降临的历史——‘人民的’历史”)。可即便是这样做了,他还是逃不掉被抛弃的命运。
因此他的沉湖到头来应了自己戏文中的那句谶语:“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
是以陈先生这么写到:“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最后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那双充满热情、不停地歌颂政治的手终被无情的政治戛然毁掉。”
与老舍相似的是曹禺和焦菊隐,经过历次运动洗礼,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在北京人艺搞出世界水平的东西的理想,这种追求与现实的不协调困扰他们几年,风吹草动之时就垂头丧气,按下不表,但是一有机遇还是抓住不放。”他们一心扑在这件事业上,却全然被当做靶子全然被抛弃和放逐,在政治挂帅的时代,最终都从人沦为一枚枚弄权者翻来覆去把玩拨弄的棋子。这种情状与他们早先时期的作品相比对,那种巨大的撕裂感和令人无言的悲恸才得以彰显。
丁陈问题在我有限的接触中,更多被划归为派系斗争问题,这一点与胡风周扬在理论层有所龃龉还不太一样,似乎确实是复杂的人事关系导致的悲剧。(参见洪老《材料与注释》对57年作协扩大会议的说明,注释第46条:“将事情导入历史清算的轨道,是周扬等在1955年和1957年批判丁、陈、冯的自觉策略;虽然与丁玲、冯雪峰等的矛盾,主要根源于现实权力分配(当时的说法是‘保卫文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巩固党的领导’)。在周扬等看来,之所以现实问题需要借助历史清算来解决,一是可能意识到所揭发的现实‘罪证’的脆弱,另一是,鲁迅在当代迅速‘政治神化’的情境下,30年代与鲁迅关系问题,成为周扬确立其权威地位难以绕开的障碍。”)
饶有意味的是,丁玲被斗下去的时候,“整个作协呈现人人喊打的斗争趋势”,甚至“有的支部建议,将丁玲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这种情况在这些年的对这段时期历史的认知中确实是独一份的,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丁本人在以往的作风上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联想到她对沈从文糟糕的态度,倒是可以或多或少理解了。但是认定其为反党集团的“结论宣布不过几个月,它的真实性就受到多方面质疑,即使是批判的策划、主持者也不得不同意对结论进行修改”(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此种情况已经预示着丁玲此后坎坷的遭际。
说来惭愧,我对丁玲的认知依旧停留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水》带来的印象,然而两篇作品都并不喜欢,实际上她由左联进入到延安的一段更是了解不多。贺老师写过专门研究丁玲的文章,未曾拜读,此后有空,当作补充。
陈先生在题记中简要剖析了丁玲的性格与处事逻辑:“多少年背运和折磨使她的处世方式粗疏和困惑,真实的她与场面上的她是有很大出入的,她自己也在为此相争和纠结,有时为了刻意突出自己的‘左’反而让自己愈演愈烈下去,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之后倒有了几分释然。”应当是很深刻的洞察。而三十年代“她与顾顺章的交谈,应该是她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心灵炼狱之一,她对严酷、没有私情的党内生活应该有所领悟。以后在山西、延安屡遭挫折,进城后又被多方围剿,不如意的事情十之七八,不被理解的事情更多。这些不适甚至是负面的阅历都给她的思想世界抹上既深重又暗灰的底色,轻易不敢示人。正因为她知悉的事情过多,又是一个天生有大局观、生性敏锐的女性文人,思想上打上了死结,因而活得很沉重,选择也很艰难,注定黏附着迷离而不能解脱的悲剧宿命。”也是十分重要的补笔。
但是即便有过此种经历,丁玲仍旧未曾完全放下介怀。在北大荒她始终在心灵上与当地保持着距离,而不断向往想要回到政治中心。她一次又一次主动检讨,但却总是得不到摘帽的答复,整个过程就像是 K 在面对城堡时所遭遇到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心理体验,其悲剧性也更多体现在其中:在一次又一次石沉大海和否定的回复中,连失望也只能小心翼翼地表达:“关于我的问题,和你对我的意见,陈明也转告我了⋯⋯我没有任何意见,虽然有过一些难过,但一想到个人的进步,离党对我的希望还很远,成绩与罪过也不可能相比。”而到后来,为此一点点委曲求全的过程也是基于不断自我贬低和损毁:“⋯⋯我不能不承认,另外有一个埋在我心底里的声音,偶然当我想到什么,或说到什么的时候,它会忽然跳出来,悄悄地向我说:‘你不配这样想,你不配这样说,你是一个坏人,你不只做过坏事,而且品质很坏。’我不得不沉默了。我想,为什么我不能甩掉这种自卑感?⋯⋯我是彻底地认识了自己的,是错了,是不好,是丑,是坏。至于面子,更没有,那面子已同我没有什么相干了。那是死了的丁玲的面子,我早已看见那具尸身漂过去了,我对那具死尸也是无情的,而且高兴它漂得远远的⋯⋯我懂得,这须(需)要我更刻苦,更努力,只有更多的赎罪,把罪赎完了,才能得到安宁。”
说到底,可能到头来谁也没能走入丁玲饱经催折的内心。她所表露的与她真正所想的之间的距离,是否也已经由某种精神的销蚀走向了与许许多多其它知识分子一样的裂解?
但我想,即便她们经过重重浩劫(甚至很多人对“浩劫”这个词本身都抱持反对意见)让自己破除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念想,但其最终能够打破的还是对某些个体的而不是整个对事业和领袖的信,这是她们这代人永也难以克服的局限,或许也是不可破除的支撑其过活的根本的信念。钱老在谈及自己对毛时代的态度时引了鲁迅《颓败线的颤动》中的一节:“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表现了他这代人既渗透在毛时代的文化脉络之中,又试图从“母体”中蜕生脱离的纠结。而对于从延安时期就跟随《讲话》而走的丁玲、周扬等人而言,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人崇拜与整个革命与民族的命运深深纠缠在一起,前者已然成为后者之所以可能的肌理,因而否认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的重塑,意味着对其存在之根,几十年如一日所坚定的自我价值与人生追求理想的毁去,因而她们即便有过如此经历也还是自觉不自觉显示出一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状态(所谓的新时期的“归来者”与“幸存者”)。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郭小川那里(想来其实真的很难说他们之间,谁的悲剧更凄惨一些)。
在某种程度上,郭小川是被强行卷入作协复杂的人事关系之中的,在被抽调之前就表达过不愿前往。张僖的话可做参照:“他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作工作劳力来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30 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带到机关。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的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
后来几经波折都想从作协这个大染缸中抽身,都未被放行。这使他与刘白羽、周扬等人的关系更加紧张,更不用说在批判《一个和八个》的时候,郭小川实际上作为了被前两者处心积虑抛出的弃子。种种遭际令他心绪极度不安。到后来需要长期服用不同种类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杨志一在回忆郭在团泊洼时这么写道:“吃安眠药有麻醉作用,吃下去了在迷蒙中得到解脱,当时就没有烦恼,像吸毒一样。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他在房里吃午饭,安眠药发作,一下子晕倒在桌上,睡了一觉才醒过来。下象棋后回房间,药劲上来了,走路时东倒西歪。这说明他苦闷到极点。”
类似服用安眠药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鲜见,林徽因、金岳霖、沈从文都有服食的经历。虽然对不同的人而言,安眠药的作用并不相同,但相近的却是这些知识分子在身体上的衰弱和颓萎。
郭与丁的不同在于他始终有着一种信念,即试图在后续的运动中证明自己的无错,这种执着其实掺杂在对周、刘、张、林等人的怨念与对“领袖”的信任之中。当然他其实是处于起起伏伏的状态之中的,在运动来临前的激越和准备大显身手的想法很快被运动的酷烈与惯性所压倒,最终退回小心谨慎与无奈消沉。那个未能落到实处的帽子其实永远悬在他的头顶,这一点倒是与丁玲既相似又不同的。对此,陈先生有更细致的分析:
“运动折腾之中或过后不断把人归类,让人在消沉之际又有一种步入正常位置的快慰,又满足于运动之后那种给人喘息的暂时平静状态。人们为恐惧所震慑,为平安而苟全,懒于深究,怯于思索,重复过着低能、麻木、简单的生活。
在运动初期暴风骤雨的惨烈之后,往往施以‘团结挽救大多数’的善后政策,让人从无望置换成轻松,从犯罪感解脱成平安感,使人对运动的结局总有几分期待,几分把握。‘文革’中大量关进监狱的人们大都靠着这样的信念支撑着。
再者,运动初期形成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心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的愤怒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这就可以理解郭小川为什么频频地感谢运动的斗争和教育,感谢党的挽救和宽大,并在长达数年间对‘文革’运动表示内在认同感。读一读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诗歌、所写的思想检查,你会感受到一种亢奋,一种顺从,一种欲跃马扬鞭的紧迫感。
郭小川身上的矛盾心态,实际上折射了‘文革’的复杂成分。”
从 1959 年被抛出到“文革”其间再度被揪斗的经历对郭而言其实是一种持续性的摧残,在一个本来并无大问题的作品中无限上纲上线的结果就是将一个正常的个体的心理防线一点点摧毁殆尽。
洪老向人们展现的 1957 年批判丁玲、冯雪峰的记录令人触目惊心:
写出《包身工》《上海屋檐下》这样的作品的夏衍在会议中对丁玲的道德评价,使用了骇人的语言,说:“我亲眼目睹的和找到一个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是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丁玲同志被捕之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就是说,冯达被捕之后几小时之内就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其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同志手里夺回丁玲。因为这时候雪峰同志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从以后的结果看,冯达的目的是达到了的。……丁玲、雪峰都有很阴暗的一面,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灵魂深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黎辛(当年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40 多年后 1995 年回忆:“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接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静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何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
种种情境并不比当时在座的各位大作家作品中的情节更光怪陆离。
陈先生对参与者的心理剖析十分精到:“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回到郭小川这里,当年愤激批判丁、陈、冯的他在被揪出之后“真的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后来几次谈到那时的心境:‘我简直几乎绝望了’、‘那几天痛苦得简直不堪言状’、‘实在不忍卒读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作品’等等。”现在读来只有深深的悲哀。郭所遭遇的与丁玲在被定性为右派之后几十年如一日在检讨书中自我审查和祈求原谅的行为其实如出一辙,都显示着庞然大物对个体人性的践踏和对精神的持续性摧残,其目的是在精神上完全摧毁后者。但饶有意味的是,曾经一度站在施暴者一方的人却都无一例外地未能躲过自己被施以暴行的那一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舍、丁玲、郭小川等人都是彻彻底底的悲剧人物。
陈先生对郭在听闻林彪事件之后所感到的震动这样分析到:
“党内高层还有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路线斗争,还有这样秘不示人、激烈的对抗过程,尤其是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臭不可闻,这种巨大的现实反差是无法让郭小川一下子承受住的。他承认已无法适应犹如海啸般掀起的政坛风暴,这直接动摇了他几十年坚定不移、誓死维护的思维定式。
很长一段时间,郭小川始终觉得没有缓过来。”
在此前他已经向读者揭示过:
“像郭小川这样对新社会充满理想的诗人、从延安培养出来的文化人是不是从这时开始有了一点一滴的怀疑?这种疑问的产生是战战兢兢的,害怕这种念头的缠绕,竭力想在心头掩饰住什么。要正视它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郭小川敢在运动关头表白自己不赞成的保留态度,并同斗争对象保持不避嫌疑的接触。他慢慢地憋出了与时代唱反调的小小声音,也有了不计后果的微弱的抗争举动。
几十年如一日的激情正在退潮,由此开始的却是痛苦万分、一步一回头的思想跋涉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付出了代价。既有跳跃,又有反复;既有憧憬,又有幻灭。”
对于林彪事件带来的震动感,钱老如此说道:精神危机如此尖锐地浮现出来:“这个事件迫使人们对毛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特别是曾经一度狂热崇拜毛泽东的青年人,更是经历一次最深刻的绝望…… 这种从绝望中引发的反思,是真正刻骨铭心的。”
“我们曾为之献出青春热血的理想,还值得相信吗?还经得起考验吗?如何看待我们亲自参与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社会、经济依据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我们的文革理解与追求对吗?”每一个疑问都近乎天问,而其背后更深的探问则是:“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
现在看来类似的天问在每一代中国人那里都存在着,这里存在着一个令人悲哀的历史循环:文革一代受到林彪事件的影响而失望,后文革一代受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酷烈事件而失望,现在生于八十九十年代的人又开始因为疫情而失望。更令人难过的却是,人们并不深究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而一味在不无引导性的主流叙事下继续负重前行,那这种前行的结果是否又将引导向另一次失望?
总有一种声音告知我们想得太多却做得太少,但我想值得怀疑的却是这声音本身:难道我们真的想得足够多了吗?更不用说,现在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太多人在麻木而无意识地做着什么事情,却忘记甚至压根不愿意思考,结果就是抱着一套现有的最广泛最被广为接受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洋洋自得。
如此看来,并不是理想主义并不存在,而是存在着的理想主义被麻木的现实与更加麻木的看客一点点摧折蚕食着。
换到自己头上,个人的精神危机发生在对现有体系的不信任和质疑,即对纯粹的不可能和必然浸染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此引出的“理想必不可能实现”的念头。目前尝试走出精神危机的方式则是试图搞清自我与中国,分别为这两个对象寻找一套认识的方法,但很显然这依旧无法阻止那种盈溢而出的虚无感,因为必不可能实现的感觉和现实是如此残酷地一遍遍回荡,几乎是每天每时每刻的复响。因此,中李老师所谓的“记得敢于去相信”在我这里也就经过了一次变动:从盲目地认定自己敢于去相信,到如今的认为如今依旧坚定地敢于去相信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值得人尊敬也极为艰难的事情。也因而更能理解,在残忍年代坚持做对的事情,确实有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痛苦与困难。后者却也是郭小川、赵树理、沈从文等人最常被人所忆及的。
在备受压抑和深感失意的郭小川背后还站着另一个永远保有激情,愿意捍卫真理的郭小川,正是这个复杂的个体在那样的落寞时节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
相较之下,赵树理和浩然分别被标榜为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的两大作家,他们的经历想来都只能令人叹息。
赵树理老实人的性格、为底层说话的处事态度以及农民出身特有的无机锋都让他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显得如此扎眼。
面对农村的现实情况和高层交付的宣传口径之间的龃龉,他无法不感到进退失据,为此被揪为典型,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
“邵荃麟代表组织者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
“赵树理无言以答,在会议构织的言语矛盾网中左冲右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会议记录本已经很少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在这种压力和威胁面前,心里的防线逐渐地崩溃,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只有无奈地低头或认同,他在想:自己真的错了吗?”
“当时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原因,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最有戏剧性的是,当他苦思冥想寻找出路的时候,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巨大的运动机器慢慢地减速,批判大会无形中被通知取消,赵树理和与会者又一次被置于不知所措、头脑空白的境地。”
“运动进入收尾,没有人肯为这些问题再去大会上批判他,整个机关失去政治性反应,一两个月前火爆的批判场面冷却了,只是变成痛苦的记忆碎片留在当事人的心里。”
“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 1962 年 8 月大连会议,赵树理才在整个形势鼓动下,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 1959 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
陈老写道:“据说,赵树理在临死前极度失望地说了一句:‘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
在这里,从钦定的新文艺的旗手到被整风批倒为反动分子的落差,个中心里滋味难为外人道。临终之前他所最终明白的又究竟是什么呢?现在读来也唯有一声叹息。
而浩然则在不由自主之中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作为文革期间“唯一幸存”的作家,看似“身居君侧”,但实际的不胜寒也少有人知,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也显示了历史的惯性是难以抑制的。
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能躲到医院里。”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尊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剩下他一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
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 1998 年 11 月 24 日口述)
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写。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 1998 年 11 月 28 日口述)
“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
(剧作家梁秉堃 1998 年 12 月 23 日口述)
勤勤恳恳写出的作品被视为跟不上时代的粉饰之作,对于一个只想潜心写作的人而言,其中悲哀又有谁知?
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查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
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关于汪曾祺,陈先生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一个补笔让我们看到当年的年轻知识分子身上的火光是如何被一点点消磨殆尽的:
1958 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
在 1957 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他觉得“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本错误事实”,成了 1958 年秋天补划“右派”的根据。他在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封信中,极为低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因为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认识上和同志们有很大的距离,心里很急躁。所以在昨天的会上表现了那样对同志们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很不好的。
⋯⋯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
当年划“右派”之后,他回家向妻子转述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他凄惨地对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过社会主义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而在摘帽后,经由特殊的契机重新被启用,汪曾祺的表现已经转为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本本分分,不敢越出雷池半步。
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分。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他没有去依附江青。
他根本不聊政治,不敢说江青意见好坏。对政治既不是老练,也不是圆滑。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跟人打得火热,交往时义气不浓。
(原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 1998 年 6 月 22 日口述)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廉 1998 年 7 月 6 日口述)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祺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 1998 年 7 月 7 日口述)
越到后面越是觉得难以下笔,索性就摘引原文了。其实无论是哪类群体,在大时代之中都显得颇为沉痛。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无一例外地如钱老所言,并不无辜。参与核心文坛事件者无一例外地既作过伥鬼又当过冤魂,而未参与者却也没有敢于发声乃至行动。反倒是唯一做了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们所不敢做的那位,在全书的最后一篇做了极为隐晦的处理,让人不禁觉得,那只巨手至今仍在头顶高悬。
最后说两点没太大关系的感受。
陈先生此书让我们能够从纯粹的文学和文学史的角度跳出来看待整个运动及身处其中的人。即是说不再将这些对象视为作家和知识分子,而自觉地将之视作管理者和政治参与者,由此去看这段历史及其中的人事,或许能打通某些卡住的关节。
第二点:80 年代初担任北京市作协党组书记的陈模在评价浩然的时候这么说道:“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重,包袱太沉。”
这个观点其实很有意思,它显示了文学管理者认为与泥土最接近的农民作家要跳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写农民,但是这种跳脱其实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如何界定他们的身份,类似的疑问其实一直出现在如今的底层乃至现在所谓的素人写作之中。当我们强调文学品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的身份影响了品质的呈现,可一旦强调起身份则又会觉得真正脱离了原本身份的那些作家写得不够代表他们的出身。
拉拉杂杂写了很多,一些曾经琐碎的思考也呈现在文字之中了,此处也就只作为一个供后续参考的研究手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