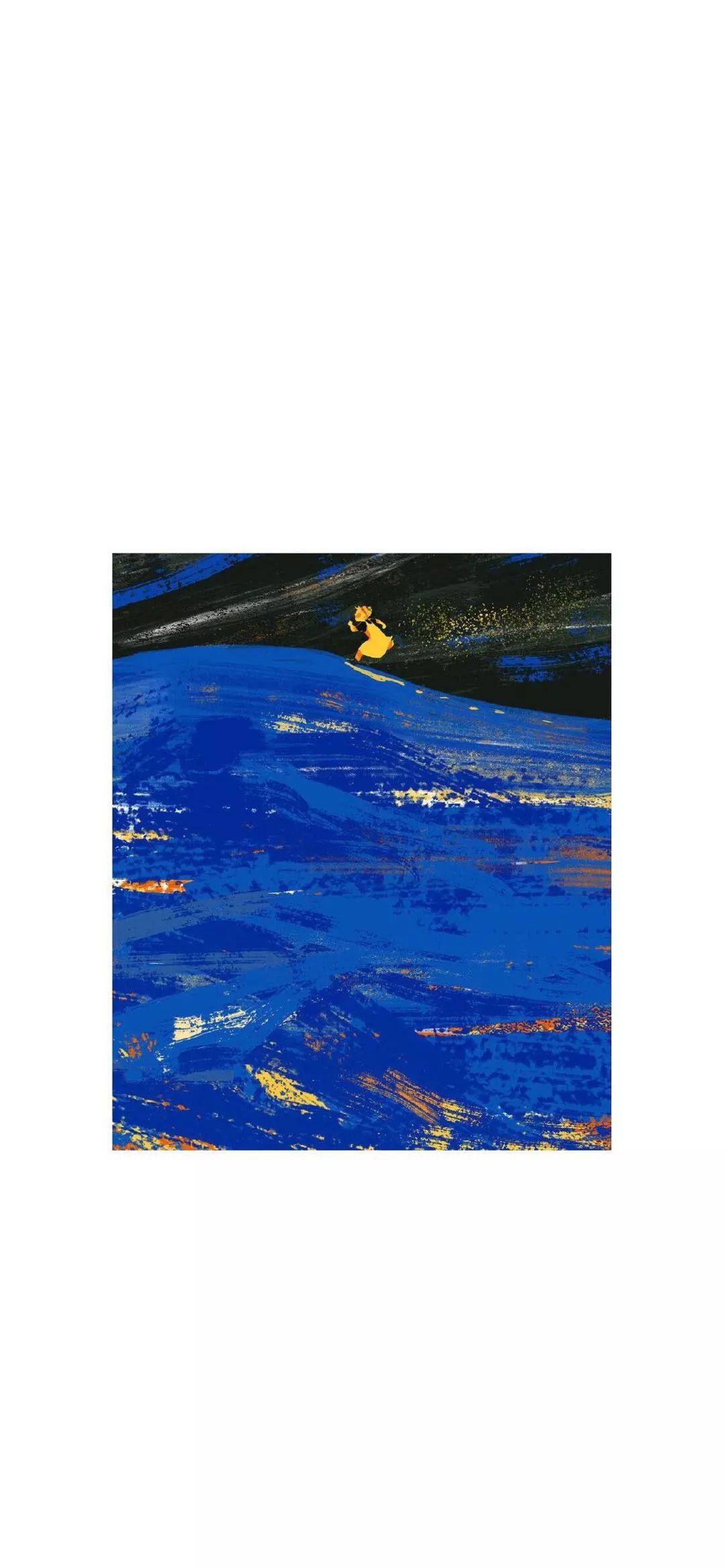I Fell in Love With Princess Peach
“说是你要来,很快的起来了,这一天一直惦记着白衬衫的袖子脏了。”——石川啄木
01
睁开双眼的时候,晨光透过浅褐色的窗帘未被遮蔽的四围挤入昏暗的斗室。即便是休息日他也无法让自己随心所欲在想起来的时候起来。
其实,意识到自己已经苏醒这件事就足以令人泄气。生物钟带来如针刺般的刺痛感,也将饱胀鼓起的睡意一下穿破,消散殆尽。
在这些睡眼惺忪的时刻,总有难以抵御的什么东西会侵入身体。有的时候是焦灼的欲望,有的时候是昏沉的暗想,抑或是来自躯体的难以回避的酸痛感。伴随苏醒,这些东西传达至脑海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钻入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会感到难以言说的疲倦。
可生活,铁面无私的生活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动着它既定的律法。它甚至不屑于告诉你,你必须在某个时刻做些什么,也不愿告诉你如果你不去做将会收获怎样的结果。好像这一切都不言自明,至少我们每个人都如此认定,也如此践行。在这些时刻,追问总显得是不合时宜的。但在他那里,始终令他感到疑惑的却是,自己究竟何时合过时宜。
翻来覆去想再多睡一会儿,脑海中却浮现着匆匆一瞥看到的消息提示。他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个人有的时候明明看到了却不想回复,又为什么在那些需要的时候坚定地秒回。在那些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在那些坐在窗前一边耐着性子写稿一边神游八荒的时光里,在他明明难以回应的时候,对方却用着一条又一条语音不由分说地挤入生活本就不多的缝隙。而当那些防备被轰炸殆尽,对方却悄然溜走,狡猾得如同狐狸,像伸手却总也捉不住的光滑的泥鳅。后来,当他从越来越少越来越短的语音中听到对方声音中夹杂的疲惫,愧疚和歉意却又总是难以摆脱。在这些时刻,他感受到的疑惑就像对方将他从沉潭中拎起的那些时刻感受到的一样多。
02
坐起身的时候果不其然感受到来自颈椎的压迫感。又想起对方对他说的那些话,是啊,没有人会喜欢一身病症的人,但是他又能怎样呢,仅凭意念和空想无法祛除身体与心灵的病灶,那是不是对他而言就只剩下被挑挑拣拣的命运,就像每一天他都在感受的那样?
20 秒加热的三明治、仍有余温的牛奶与鸡蛋。一边发愣一边机械地依凭本能噬咬。
每一次打开蓝色与红色软件,就像一头扎入欲望的深池,令人刺骨的生冷和百无聊赖的荒芜感如同漂浮在光照下遍布空气之中的尘埃,附着在身上,摆也摆脱不掉。但他内心更多感受到的是恐怖与无所适从,而不是兴奋和期待。就不提那个在既定程式之后该如何继续开展对话的“天问”。他到现在都没搞清楚究竟是既定程式的语言模式限制了他的思维还是他本就被磨损消耗殆尽的思维导致他无法让自己跳出那个模式。他只知道自己与其它人一样,也无话可说。但是他又为何要在无话可说的情况下去追觅自己的猎物,或让自己成为被他人追觅的口食?他不知道。
在逐爱的名义下一次又一次自我贬损,一次又一次自我异化,将自己降格为橱窗前的商品,这还不够,更确切地讲,是一个有瑕疵的廉价待售物。两件事物构成的关系何以如此稳固,明明这样畸形却表现为无法动摇的三角?在一个又一个你好和换照之后隐伏的是一次又一次点亮又熄灭的心灯,在一次又一次为谁先发照片、多少秒撤回的心理博弈之中,他感到无可言说的倦怠和无趣。到底是谁在为自己画地为牢,又是谁试图在这些本就存在的囚牢之外将那些不愿画地为牢的人赶入其中?
在喝完牛奶的那一刹那,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放弃继续喝牛奶的习惯,更意识到自己刚刚敲出的你好毫无意义。
03
好几次夺门而出一次又一次在越来越慢的电梯里点亮屏幕焦躁不安地一遍又一遍看着一秒秒流逝的时间。
在这些时日里,追赶早八的公交车似乎已然衍化为亘古未变的属于自己的日常。每一次迈步飞奔,每一次气喘吁吁赶上公交的时候,那种打心底冒出来的“赶上了真的太好了”的感受都让他有种莫名的陌生感。在抵达公司之后,回想起这些时刻的日常中,记忆中的自己仿佛在一点点褪色,至少有一种疑惑根深蒂固挥之不去,他知道只不过是因为打心底里不愿承认那曾是自己。但他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抱着那些曾经的一切不愿放手,就像每一次夸夸其谈之后都会为自己方才无与伦比的自矜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一样。相比之下,这种紧迫感和焦虑感更像是但丁在人到中途遇到的恶兽一样,在这样的虎视眈眈下,他总能觉得出不寒而栗。
但也因此,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无法割舍对对方的那种眷念,即便明知无法获得回应,但还是愿意一遍一遍在心底重复如云的念想。因为对方有一种轻而易举将自己提溜起来的魔力,这让他有一种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坚信,坚信至少在这一刻,从对方嘴中说出的话语所言非虚。就好像时间飘摇了又飘摇,他终于再一次寻回了那份被飞驶向前的四号线遗落下来的支托感。明知对方无意赋予他,但他仍顺遂着本能让这份终会回归虚无的安稳在空落的荒野中肆意滋长。
坐在车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脑海中逐渐灼烧至沸腾,他该如何将这些时日与这些新的情感联结恰当地安放?
04
每一次在列车上坐下的时候,他都期待着这个时刻能够被拉得足够长。封闭的车厢和嘈杂的环境似乎天然地赋予了他一个阻隔一切外来消息的自然而然的屏障。他也因此意识到,自己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当然,听过闫老师对《地铁》的分析,他不会不知道这种想法本身荒谬透顶,可是似乎比起其它事情而言,这种荒谬反倒能够获得一定的自洽。他也就因此顾不上那么多了。
其实,如果没有该死的晕车和头疼的话,他本该更喜欢坐公车巡游。就像在没有工作也不愿复习的那段时日里他曾经做的那样。
坐在座椅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的时候,纷繁杂沓的思绪轻而易举将他缠绕,但作为主轴的,永远都还是那种陌生感。他无法不对这个城市感到一种陌生感,说到底是所谓的似曾相识,但它最终导向的结果却是一种惶惑和惊惧。就好像他从来都未曾看到过这座城市真正的面貌,就好像他无法真正被剥开也从未真正直面过的内心。每一次漫步在街头,他都无法驱赶这样的无措感,这个本该在字典上被称之为故乡的城市,当他放眼望去的时候却无法不将它视为异乡。他曾面对和经历的一切,那些历历在目的“风景”无一例外地流散消逝了,剩下的部分如同不合拍的拼图被安置在本来不该属于它们的位置上,尽管拼凑得严丝合缝,可真的放眼望去才发现,不过是拙劣且卑俗的模仿。
也是在那些冬日阳光照耀下漫步街头的时日里,他第一次意识到本雅明所谓的城市漫游者是在以一种怎样的目光审视他步进时四围周遭的一切。而他也因此挪用误用他所谓的“光晕”,将它置于自己的语境,并视为一种对旧时无可挽回和追溯的记忆的指称。
由此观之,兔起鹘落的鸽群、摇落金黄的银杏、干瘪枯竭的秋草、随风荡漾的芦苇,嬉皮笑脸的行人、嘈杂喧嚣的孩童,都换不回尘封老照片中烈日下穿着开裆裤一步步走下台阶的自己,也换不回那些已经泛黄却仍被定格了的鲜艳亮丽的花朵。这一切就像他又一次抵达 CBD 湖畔的时候再也感受不到少时夜间与亲人初见此处的那种兴奋感;就像他又一次进入中原万达时再也无法获得的从前感受到的那种繁华和叹服;就像面对空旷而不复往昔的二七广场感受不到曾经天桥上人来人往的热热闹闹。
作为百无聊赖的漫游者,他出行本是为了排解苦闷,但最终收获的却总是更多更为复杂的情绪。
如今看着照片里小时候笑得无比灿烂的自己,他无法理解自己何以成长为现在的模样。
05
在与“小狗”分离之后的这些日子里,他尝试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一路追逐,全心全意向他表示爱意的;也有显露控制欲和同样不愿表露自己真实感受的;有自视甚高想让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也有无所谓其它只想在肉体上保持关系的。
他平静地接受一切,感受着每一次情绪和身体上的劳动所带来的付出与回报。只不过他发现自始至终自己似乎难以说出任何一个拒绝的字眼。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接触中,与其说是他因为某种感情的激动让自己陷入,而不如说是一种长久以来的惯性将他拉入其中。说到底,他怀疑的是自己究竟是因为真正对对方有某种感觉还仅仅是想要让自己处于一种“被爱”和“可以去爱”的状态里。在这个意义上难道他不是在自伤的同时伤害他人吗?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告诉晓洺在阅读林奕含的时候他无法让自己不去将整个自我代入到房思琪的处境。尽管明知这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情境,作为男性他也没有任何资格去说自己能够切身体会到女性深受的那种压抑和痛苦,但是他却无法从房思琪的遭遇带给他的感受中脱离出来。其实,他不敢,也不愿意去更进一步思考他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了现在的自己。他怎么会不知道只有将被压抑的挖掘出来,才有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他却没有勇气。
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深知这一点,在面对“小狗”的逃避和语焉不详的时候他才无法真正让自己对他感到憎恨。因为本质上,他们是一类人,虽然他厌恶自己,否定自己,但他怎能让自己在已经损毁自我存在的根基的情况下再去进一步憎恨、否定自己存在的另一个根基?
可能也是这样,他才会硬着头皮继续去读那本冗长无趣的《魔山》,不只是因为他的较劲、不知变通的死磕心态,也是因为他真正从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看到了一种与自己类似的状态。魔山在此真正成为一个缩小了的社会的展演,成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接受教育的“大学”,这本书也因此成为一部教育小说,让人徜徉其中,采撷自己最终认可的那份思想。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他当下正在接受的这些“情感教育”之中。
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始终伴随着他的其实还是那样一种不安,一种精神上的流浪感。这其实是对他整个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核心要素。只是前些年在子宜身边的时候,这种感受被相当程度地掩埋和化解了,而当他与子宜分离之后,这种感受就成为一种梦魇,时刻萦绕,加之他本身作为一个活在过去的人,这种失衡和不适带来的冲击要远比他想象中更大。其实,无论是从他与“小狗”的接触还是与那个人的交流中都能发现,他之所以愿意倾尽全力正是因为他从接触与交往中获得了某种刚刚说到的“支托”。问题在于如何自我提供这种支托而不再依靠他人。在他目前的思绪中并不存在一个可行的“解”。
当然,他所收获的另一个教训是,究竟该以怎样一种心态对待他所属的这个族群中的其它个体:
如果追溯起来的话,最初主动谈及这一点,还是在武汉旅游时跟晓洺的交流;而更早,可能在与“小狗”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他当时读吉野和魏老师作品留下的理念在“小狗”身上得到了验证,最后经由自身再度被验证。只是那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会如此重要,后来经过那个人的点醒,这一点到成为了一个考虑得相对充分的问题。其实就是他在读书笔记中提到的那些:尝试在族群中建构一种超越朋友关系与恋人关系的以情感联系为纽带的新型关系。而要想构建这样的关系,重要之处在于秉持开放的心态。
但是说到最切身的体会,那可能还是“拥抱要深”。
06
让自己不陷入消沉是如此困难,在这种关系里他无法不让自己感受到情绪是猎人而自己是猎物,他能时刻感受到它蛰伏在身边透过凶骇的目光逼视着自己,等待着趁虚而入,一击毙命。
与此同在的还有难以言喻的矛盾感。
精神的分裂客观地呈现在文字的分裂之中。他无法做到在工作中使用一套自己完全不认同的表述的同时,在其它的时刻又用另一套与之截然相反的表述。每一天都会让自己陷入某种难以言说的崩溃,正是由于在写作的时候他一边要让言语动听合理、论述条理清晰,另一边又在内心告诉自己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冠冕堂皇大言不惭地表述自己并不真的相信的那些东西,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不会因此感到自我撕扯和挣扎的痛苦,而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又有多少他所珍视的人能够理解?事实却是,前者榨干了他的输出功率和能力,令他在面对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的时候无法言说,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语。
他只能在脱离那个环境的瞬间让自己被或是更为宏大、或是更为原子化的文本包裹,但越是这样他越是感受到自己在被相反的力撕扯、扭结着,而且更令他感到恐怖的是,他无法不去担心自己是否会在日复一日的灌输和洗脑下让原本的“自己”被消蚀殆尽。他要如何保全自己,保全那个他珍视的“自我”?
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他在对话沟通时不经意间连续的叹息,成为了他坐在列车中面对文字时即将夺眶而出却最终总是被抑制住的泪水,成为他走在回家路上望向晚霞时希望它再多停留一些时刻的妄想。
但这些东西在那些与之交往的人眼里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可以被尽情取笑的,被各种标签所裹挟、指认到面目全非的,况且如此感知的不只是“他们”,几乎是所有人,是子宜、是“小狗”,也是那个人。
但是他又要如何向他们诉说呢?又要如何告诉他们这些感受对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失去它们他就会怀疑自己是否还真正活着呢?
或许他更担心的是,在他还没有机会出口,他们就已经离他而去了,这也是他面对的现实。
所以他怎么能够不陷入到某种世人所理解的根深蒂固的消极和悲观情绪之中?他又怎么才能告诉对方,这种悲观和消极才是真正对这个世界的热爱,是他想存活下来的证明?
Please don’t tell me to change
I’m more than content living this way
And I hope some day
That you will feel the same
How about me
If you could change(change)anything
Please just stay the same
Because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