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证实的叙述——浅析《哈姆莱特》中老王死因的可信性
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总能够让人生发出诸多的理解,它们所包蕴的细节和内容总是足够充分因而具有出广阔的探讨可能。正是在这种不断地阐释过程中,优秀的作品逐渐被世人经典化,最终成为留名青史的不朽著作,而《哈姆雷特》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同王子在那个时代中的身份一样——尊贵显赫且具有超前的魅力,经过四百年的淘洗却仍在不断绽放出熠熠辉光。对笔者而言,对它的每一次重读都如同叩开一扇崭新的大门,每一段人物的发言背后似乎都能挖掘出深刻且细致的意义,而对参考文献的阅读则更进一步地将一些笔者曾经从未思考过的细枝末节推展到了自己的眼前。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鬼魂所言的被谋害的方式是否真的可信——并试图阐释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意义。
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有关老哈姆雷特的死因,我们所能够掌握的只有鬼魂所言及的内容,而自始至终克劳狄斯都没有明确说明自己杀死老哈姆雷特的方法,这就构成了第一个问题,即鬼魂所言究竟是否可信?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在鬼魂说话的时候,除哈姆雷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在场者,因而我们也要对鬼魂是否真的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客体提出质疑,可以说这个问题同前者密切相关。然而无论如何,哈姆雷特在剧作之中都展现出一种近乎全知全能的特点,莎士比亚做出这样的安排必然有其深意,这也正是笔者试图通过对前两个问题的探讨所真正想要关注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回答前两个问题,这牵扯到对哈姆雷特与鬼魂相遇时情况的分析。
当哈姆雷特第一次听闻父亲的亡魂在游荡的时候,不安和怀疑几乎是下意识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想到“这里面一定有奸人的恶计”并且说出“罪恶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发现,虽然地上所有的泥土把它们遮掩”这样近乎预言的话语,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早就对父亲的死因有所思考和怀疑。接下来,他在见到鬼魂时的第一反应是精神上的极度紧绷和激动,他高呼:“我要叫你哈姆莱特,君王,父亲!”这种态度体现出他没能够完全排除父亲对他的影响,而“不要让我在无知的蒙昧里抱恨终天!”则表达了他对父亲为何现在出现以及父亲突然薨逝原因的渴求。而当鬼魂让王子随它而去时,哈姆雷特身上这种反常的举动并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更加突出,面对好友的劝告他表现出一种无畏和无惧:“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至于我的灵魂,那是跟它自己同样永生不灭的,它能够加害它吗?它又在招手叫我前去了;我要跟它去。”这里的生命和灵魂被哈姆雷特分隔开来,可以看出它们所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面向,对这一点在后文会有更详细的讨论。这时的哈姆雷特已经不再能够听从任何建议,身为理性化身的王子在这时反而完全失去了自己所具有的理性,正因如此,霍拉旭才叹息道:“幻想占据了他的头脑,使他不顾一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哈姆雷特在面对鬼魂时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反常性,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鬼魂是一个导火索,它点燃了哈姆雷特内心长期存在的将燃未燃的火药,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预兆,这种反常似乎同他的结局构成了隐隐的呼应。
莎士比亚接下来构建了一个类似密室的场景,他排除了其它因素的干扰,将王子和鬼魂单独置于其中。在这个情境中,鬼魂向王子提出了复仇的要求并且叙述了自己被杀害的经过,照它所言,行刺的过程应当如下所示:
“当我按照每天午后的惯例,在花园里睡觉的时候,你的叔父乘我不备,悄悄溜了进来,拿着一个盛着毒草汁的小瓶,把一种使人麻痹的药水注入我的耳腔之内,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地流过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一般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便立刻发生无数疱疹,像害着癫病似的布满着可憎的鳞片。这样,我在睡梦之中,被一个兄弟同时夺去了我的生命、我的王冠和我的王后;甚至于不给我一个忏罪的机会,使我在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受过临终涂膏礼以前,就一无准备地负着我的全部罪恶去对簿阴曹。”
它对克劳狄斯施罪的过程细致描述,在宣告的过程中满含激怒和愤恨的情绪,它毫不理性因而也就显示出明显的破绽:既然如它所述,整个过程中老哈姆雷特都在睡梦中不曾醒来,那么如此清晰的过程又是如何被它知晓的呢?自然我们可以将之归于神学宗教的全知观念,但从这种近乎第三者在场的叙述本身仍旧无法完全消解我们的疑虑。如果我们对此按下不表,那么也应当注意到,鬼魂所说的话得到了哈姆雷特的迅速回应(“我的预感果然是真的!我的叔父!”),既然我们的王子是从威登堡匆匆赶回,那么他会产生并坚信这种预感实在称不上是合乎常理。在这里哈姆雷特身上已经体现出一种特异性,这种特异经由鬼魂的验证显示出神秘色彩,而听从鬼魂话语之后的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进入了疯癫的状态,他的自白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近乎于宣泄,因而给人以饱满至充溢出来的情感体验;神秘色彩同非理性、非节制情感的结合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王子在见到鬼魂的时候究竟身处于怎样一种精神状态。通过对剧本的考察,不难发现,在整个第一幕中他都深处于悲伤和极度的无奈、痛苦之中,没有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甚至他也不能在外表上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克劳狄斯和乔特鲁德要求他收起自己的哀容),这种压抑带来的苦闷同老哈姆雷特在他心中的形象一起构成冲溃精神屏障的奔涌洪流,他无法节制——最起码在内心之中他做不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同鬼魂的单独会面才显得极为可疑。同样可疑的是,尽管鬼魂也被霍拉旭、马西勒斯等人目击,但他在最终述说时却偏偏挑选了一个并非在三人同时在场的时刻,正因如此,即使鬼魂本身可能确实存在,但在王子所处于这样一种精神不稳定的情况下,它所说的话究竟是否真的是剧本中所呈现出的样态就令人感到难以确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鬼魂——确切地说,与哈姆雷特单独相会的鬼魂——很可能是哈姆雷特当时内心状况的一种投射,是传统压抑机制失灵后所构成一种的混乱状况,它所强调的对克劳狄斯的复仇则更有可能是哈姆雷特自己内心潜意识的强烈呼唤。
如果挪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论,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对此加以解说。通过对文章的阅读不难发现,在王子眼中老哈姆雷特是“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同克劳狄斯相比“简直是天神和丑怪”。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的厌恶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克劳狄斯对他的侄子则显示出极大程度的友好和关爱,两人对待彼此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即强烈的敌视与讨好式的温和——构成了强烈的张力。哈姆雷特对于老王和新王的不同态度似乎恰好对应于俄狄浦斯理论中的两个阶段——由对父亲的崇拜和遵从向对父亲的反叛和攻击转化,只是这种攻击最终形成了实质上的拔刀相向和真正的刺杀。而鬼魂的出现则是将这种转换推进的重要推手,因而哈姆雷特也就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俄狄浦斯。
残雪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有相似的表述。她认为哈姆雷特早已“萌生了抛弃由阴谋构成的世俗生活的想法,又还没有彻底了断来自尘缘的冲动”,致使王子产生这一想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不愿沉沦于这个社会,正因如此,他的身上显示出一种分裂性,同台词中身体和灵魂的分裂相似,这里的分裂实际上是世俗与精神理想的分离。老哈姆雷特的死亡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开始,而鬼魂的出现和话语则为哈姆雷特抛弃世俗生活提供了精神动力:作为鬼魂登场的老哈姆雷特给意图脱离尘俗的王子下达了难以完成的任务——将他深缚于世俗的复仇之中,为了完成这种复仇,王子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分裂开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使他陷入疯狂的根源;而与他相关的人的亡逝则是他不断斩断自己同世俗联系的过程。然而,在王子的心中,死亡并非是他的最终目的,相反,对生的企望和挣扎着存活才是他感到痛苦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在最后关头要求霍拉旭活下来传述他的行为与事迹,这一行为正标志着他对生的无限眷恋。然而生却无法达到——复仇这样的重任以及残酷衰朽的现实生活都在迫使他走向自己愿望的另一边。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思考莎士比亚为什么让象征着老哈姆雷特的鬼魂来充当推动者?她指出“鬼魂”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是哈姆雷特理想的化身,之所以只有他能见到“鬼魂”,是因为仅有他怀有觉醒者式的观念;而存在于王子精神世界中的老哈姆雷特是其自身人格的对象化,“是人要作为真正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不懈的努力之象征”。[1]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总的来说,在笔者看来,鬼魂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主体,相反它实际上是哈姆雷特的一种精神意识的反映。正因如此,笔者认为鬼魂所言的谋杀方式有其不可信的一面,之所以产生这种怀疑最大的原因就在于鬼魂的话实在是“孤掌难鸣”,全剧明显涉及到与谋杀相关的情节的还有以下两处:
首先是在戏中戏中,无论是哑剧还是正剧都模拟了克劳狄斯毒杀老哈姆雷特时的情境。问题先出现于哑剧结束的时候,克劳狄斯在此时以一种相较平静的方式发出疑问,格雷格认为他似乎是错过了整部哑剧的重点,因为倘若他几个月前以同样的方式谋杀了他的兄弟,他很难对侄子说“里面没有什么要不得的地方吧?”并且即使在这个场景之后,在剧中的任何地方,他似乎也没有担心被除了上帝以外的任何人发现。[2]继而是在克劳狄斯做出明显举动的正剧演出过程中,在戏剧进行到谋杀的情节时克劳狄斯反映出鲜明的激动情绪,并且气愤而归,这影射了他有一定的心事和隐瞒。但问题在于,他在发出这一举动之前哈姆雷特才刚刚添油加醋地将演出的内容进一步加以叙述,因而不能够排除表现出过度激动的哈姆雷特才是戏中戏场面破裂的真正原因这一可能。而当国王做出尽快将哈姆雷特派往英国的决定时,莎士比亚又在这里打了一个幌子:他并没有清晰地指出克劳狄斯之所以要把哈姆雷特送走的真正原因,反而还是刻意地混淆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吉尔登斯吞向他汇报了哈姆莱特不满足于现在地位而意图篡权的缘故。因而在戏中戏这一桥段中,我们所能得到的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观点。同样的,在克劳狄斯忏悔的情节中他只承认了“我的灵魂上背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但是对于作案手段仍旧没有提及。即便是最终哈姆雷特亲手血刃他时,王子所做出的控诉仍旧是模棱两可的“败坏伦常、嗜杀贪淫、万恶不赦”。正因如此,仅就全剧原文所显示出的内容来看,克劳狄斯杀害老哈姆雷特的具体手段仅有我们的王子一人所知悉,而他所获得的来源却是可以被视为是他意识反映的鬼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莎士比亚为哈姆雷特赋予了先见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全知性。这种全知与先见性在整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展现,除了此处之外,它同样体现在霍拉旭告诉他见到鬼魂之前,他所言的“在我的心灵的眼睛里”见到了老哈姆莱特;体现在前往英国的“海上历险”过程中的那个“无法做梦”的不眠之夜:在这个夜晚他发现了密信同时预感到第二天所遇见的“战争”(即海盗劫船);体现在他对自身名誉将受到损伤的预见性上:他让霍拉旭活下去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然而霍拉旭所言的“奸淫残杀、反常悖理的行为、冥冥中的判决、意外的屠戮、借刀杀人的狡计,以及陷人自害的结局”这些内容似乎只关注了消极的一面,同时也并非哈姆雷特所强调的自己的“人生故事”,因而他所担心的名誉问题似乎还是没能够得到他所希望的保障。[3]而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在笔者看来实际是莎士比亚一定程度上将自我融入角色的结果,可以说哈姆雷特是作者的艺术自我现身,通过对这样一个人为建构起的人间楷模的亡逝过程的书写,莎士比亚所意欲达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唤醒目的。
十七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的表面繁荣下已经潜藏着诸多危机: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圈地现象也逐渐在英国国土上展开,受此影响,众多农民沦为赤贫,而对封建制度与传统教会的瓦解又造成大量人丁的出走,工商业主对劳工的残酷压榨剥削则使大多数工人陷入绝境;社会方面,强大起来的清教徒势力对人民的生活方式横加干涉,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的中心”逐渐转化为马基雅维利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从而使得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也不复存在了。除了《哈姆雷特》中对人世间“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的评论之外,莎士比亚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对这种黑暗衰朽的社会现实加以尖锐的揭露,《李尔王》中葛罗斯特所言的“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成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坏……我们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只有一些阴谋、欺诈、叛逆、纷乱……”《麦克白》中作为贵族的洛斯在面对统治时也不得不噤声:“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然没有一定的方向。”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境况,而反观作者个人的情况,那一时期他也处于对死亡的沉思之中:父亲和儿子的先后逝去或多或少地使得他对生死问题更加看重,而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和延宕本身所体现出的对生的挣扎渴望似乎可以被视为这种思考的反映。正如前文所述,哈姆雷特将自身的分裂归因于他对现实世界的无望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之间的不能两全:他在完全没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赋予“重整乾坤”的使命,这就构成了他的矛盾,他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却感到深深地无能为力。他拥有尊贵的身份、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向善的改变之心,可以说他本身就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构建起这样一个美好的楷模,让他陷入无尽的痛苦与自我纠缠之中,他的疯癫之所以能够骗过其他人是因为“假中含真,真中带假”,而他的毁灭亦是被设计好的:莎士比亚不认为英雄能够仅凭一人之力力挽狂澜,但英雄的挣扎却足以令人为之动容,尤其是通过戏剧这种极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形式,我们实在不能相信他是无意为之的,正因这份有意,哈姆雷特的死亡才显得悲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在戏剧的最后同霍拉旭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他为世人描述的丹麦王子的故事最终顺遂了哈姆雷特的意愿,当然,也顺遂了他自己的意愿,正因如此,《哈姆雷特》才具有无限的魅力,它已经越出了文学的边界进入了生活和文化——构成了一把精美动人的钥匙,从而使我们得以更好地进入并理解那个时代,甚至说是一切与那个时代相似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参看残雪著,《地狱中的独行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7-138页、第150页。
[2] 参看Alexander Welsh,Hamlet in His Modern Gu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35-37.
[3] 参看赵山奎,《<哈姆莱特>中的书信与克劳狄奥之谜》,《国外文学》,2016年第1期。
[4]本文涉及到对剧作原文引用均见:《莎士比亚全集(五)》,(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最后是一小段碎碎念:
我不得不说这篇费时近一周的lachicken读书笔记实在让我难顶,实际上本应阅读更多的文献从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细致地剖析,但却碍于战线过长和剩下的憨批论文过多最终在此不了了之,因而可以看出最后的对于莎士比亚本人和时代背景的分析显得十分随意和琐碎。(实际上选题本身就很随意,毕竟只是读书笔记QwQ)
然而写作的诡异性在于,在一开始丝毫不想动笔的情况下介入其中,随着理解的更加深入和阅读面的更加广泛,渐渐会被这种细枝末节所吸引,最终沉浸在对语句和观点的提炼之中,这种感觉同样在最后一段的胡言乱语中得到体现。
我个人并不喜欢莎士比亚,也从来不热衷于对文本进行细读,说实在的,这份工作让我感到窒息和乏味(去年分析维特的时候我差不多眼睛都快看瞎了)。很难说我们在做的这些分析,对这些细枝末节的工作的考量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或者应该这样说,仅就我们这些学术垃圾而言,在试图拔高研究的意义的过程中总会遇到某种阻碍,因而最终总是难以达到引言所提出的目标。但身处这个地方,我们却不得不这样做,这是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是文学修习者的必修课。
我一直认为对一门课程的学习——尤其是这种导读课程的学习,至少作为学生我们要能够从中获得些什么,无论是对这个领域的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还是对于一些研究方法的掌握,抑或说对这个问题所能涉及到的点的启发性介绍。授课与讲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使听课或听讲的人能在相较俭省的时间中收获更大容量的知识,建构起对所讲解的领域的初步且足够多的认识。这并不是在说听了课就不用阅读,在我看来,阅读是更全面且深入地介入问题的方式,它同听课带给修习者的并不完全一致。正是站在这个角度,我重新审视这一门课程,似乎留给我合理且被“允许”的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有叹气,一周的阅读收获到的并不很多,但绝对超过了十周课程的所获,只是这了解仍旧十分局限,因为每一篇要书写的文章所留给你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超出限度就意味着对其他文章的削减,要对这种平衡拿捏有度并非易事,正因如此你所能收获的东西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自然要比从正常课堂中所收获到的片面得多。另一个问题在于,即便你上交了如此多的论文,最终所得的仅仅只是一个黑色的宋体阿拉伯数字,你压根无法确定你的文章是否被认真对待、是否真正值得这个数字——这种形式如同将你置于黑色的真空,什么也无法期盼什么也无法收获,这就是很多人三年以来仍旧停滞不前的原因,这实在让人感到无奈。
最后是一句忠告,尽管关注这个号的人并不多,更没什么学弟学妹:如果你真的喜欢莎士比亚或者说真的想要了解莎士比亚的一些内容,这门课可能并非你最好的选择,或许你应该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学着“自主学习”,我知道这很令人悲哀,但面对荒谬的现实,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妥协。




.jpg)
.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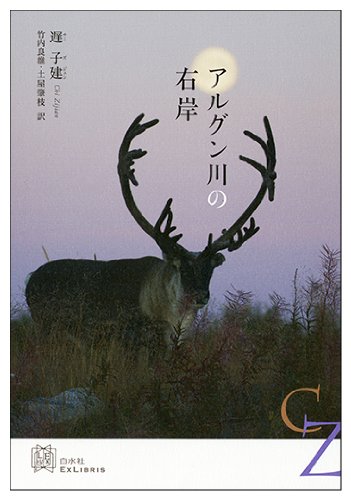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