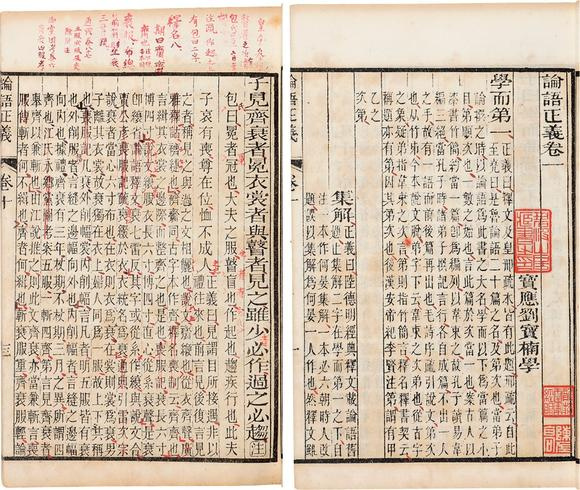《医生》——创作阶段转变过程中特殊的记忆书写
写在前面:
自从课程结束后一直到现在,都对要不要将本文放上来这件事颇感犹豫。本文作为一个小组作业,最终以报告形式呈现,所以摘要之类的并未完成,更多以视频念稿的体例来做,只是由于需要提交文字稿件,学术规范还是需要严格遵守。考虑到从选题、写作到最后的报告其实都是我核心负责的,在收到各个部分之后也由我从头到尾的润色和增补,很多内容也都进行了重写。思索再三,还是借此机会发上来,暂做保存。
前些日子,偶然发现路老师已经离开学校到北大教书,一时颇多感慨。真切地感到故去的时日确实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最后也专门重新找回老师曾经的评语,以作留念。
考察沈从文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初所创作的小说不难发现,在他书写湘西地方的众多文章中有着一种可被称为“记忆书写”的创作倾向,这些笔墨涉及到他早年在湘西的生活经历,不仅有对儿时记忆的复写(如《福生》《瑞龙》),而且包括后来从军时四处迁徙的经历记录(如《山道中》《黔小景》《更夫阿韩》《一只船》等),可以说这样一种“记忆书写”在这样一个创作时期成为值得被关注的重要现象,而其中《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以及《医生》由于其鲜明的特殊性成为我们关照这一现象的一个切入点。
一、《医生》文本分析
在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之前首先让我们对文本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
《医生》[^1]一文完成于1931年4月24日,在同年8月10日的《小说月报》上刊载。小说以白医生为叙述主体,通过白医生之口讲述了他被绑架进入山峒,被一陌生男子要求给已经死亡的女子诊治,妄图使女子复活的经历。而同样的故事,也曾经出现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2](1930)、《清乡所见》[^3](1934)两篇故事中。
尽管创作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医生》《清乡所见》。但三个文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却与顺序不同。最晚发表的《清乡所见》充当了另外两篇小说的本事,文本从沈从文的视角出发,描述他早年在湘军行伍间所听到的故事,可以说是他“本我”记忆的真实书写,同时它提供了整个故事的最终结局。而最早发表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则一方面是对本事的虚构化重述,另一方面其中的情节亦可以被视为《医生》的背景——文中提到的“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以重生复活”,这样一个地方传说的提出,成为支撑《医生》这一故事发展的关键:正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医生》中出现的神秘男子才会将尸体偷出并掳走白医生为她诊治。
可以说,沈从文对三个故事文本的书写促使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到了完整的呈现,但即便三个文本有着密切关联,沈从文对于这同一件本事却出人意料地采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并且每个文本在故事上侧重、人物、情节设置、主题表现以及叙事方式等层面都有所不同,在这里尤为突出的正是《医生》这篇位于中心位置的文本。下文笔者将通过与其他两文的对比,分析《医生》作为特殊的记忆书写文本所呈现出的特异性。
首先我们关注内容方面的特异性。
从人物设置上讲,《清乡所见》中除了“我”、押送的士兵,就只有现实中临刑受死的跛脚豆腐铺男子,而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后者的形象又被一分为二,成为的瘸子号兵和豆腐铺老板,继而在《医生》一文里,“豆腐铺老板”进一步成为主要角色,同时沈从文又虚构了一个白医生,并以白医生的视角来补充男子(后称“癫子”)偷尸恋尸的情节。在这里,医生一职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与执着于死而复生这种落后神秘观念的男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人物设置上透露出强烈的冲突。
从情节设置上讲,第一是女子死因不同,在《清乡所见》中女子是病死的,而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医生》中改为“吞金自杀”。第二,男子的结局不同:《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从本事中被处死改为了隐晦的开放式结局,而《医生》结尾则是以医生的故事流传开来收束,这种改动并不再过分强调真正的生死和人的归处,也不再强调男子为情所做出的行为带有的某种神秘性,反而转向对“传奇”的瓦解这一角度。第三,感情的表现方式不同: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神秘男子的感情是隐晦的、克制的、不为外人所发现的;到了《清乡所见》中男子则是清醒,但是因爱他并不畏惧死亡,他的沉默与微笑是对于世人的嘲弄;而《医生》中男子虽然不言不语,但行为几近癫狂,只有复活女子的愿望,于无声处听惊雷,可以说,《医生》是三个故事中感情最浓烈、叙事节奏最强烈快速的。第四,在情节上最终强调的部分有所差异:《清乡所见》是为了强调这件事对个体带来的极大触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则将爱情作为贯穿全文的内核,《医生》则不然,无论是男子把医生掳走去救女子也好,还是医生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的女子已死无法救活也好,可以说它更注重对“死亡”这一问题的书写。
从主题上讲,《医生》是三篇故事中反讽意味最强的。《医生》一文通过医生的视角描述神秘男子想要复活女子的言行,虽然外层视角是第三人称,但是内层则为第一人称,这样的设置就使得医生看待神秘男子的态度、众人看待医生的态度形成截然不同的反差。男子的行为的确荒谬,但在山洞中的医生必须服从于他的命令,因为男子是强权的存在。但是离开山洞后,男子则失去了话语权,被视为疯子,他的行为受人指责、讥讽,这便是“权威者”角色转换带来的话语权的失衡,也是作者反讽的对象之一。此外,医生失踪数日便被认为是死去,竟还给他开追悼会,而医生这段近似“聊斋”的叙述并不为人所相信,便又产生了话语权的失衡,再次达到了反讽的效果。与之相对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立足于世俗与情爱追求,《清乡所见》落脚在疯狂与清醒的嘲弄,《医生》虽仍强调了情欲爱恋的书写,但它是依附于“死亡”这个文本中位于核心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事项的,而其主题却落在由爱情而产生的美好人性通过现代社会语境的转述而转化为世俗化了的“传奇”这一现实,最具反讽意味。
其次,三个文本的形式构建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异性,总的来说,融入了许多写作技巧的两部小说,不再像自传里记录的故事一样平铺直叙,在故事的层次感和情节设计上都有了很大改变,沈从文巧妙的叙事方式也使得原本猎奇骇人的故事显得更加神秘,更令人体会到一种荒谬、奇特的氛围,其中尤以《医生》更为特殊——这构成它特殊记忆书写的另一个方面。
从叙事视角上看,《医生》是三个文本中唯一同时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与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作品,在小说里,沈从文通过“叙事套盒”转换了叙事的方式,从而使文本出现了多重视角,如主题处所分析的那样,多重视角产生的不同声音强化了文本的讽刺意味,同样也丰富了文本的内在意涵。刘潇雨的文章从这一视角出发,指出《医生》的叙事特点有三:
1.精心营造的“说——听”模式:听者R市众人的身不由己和说故事人白医生的迫不及待已然颠覆传统说故事的场面,别扭的语境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讲述的故事,听众是被虚化的,面目模糊的;而医生的讲述则直面的是被人格化了的听众——R市一群退走不得的众人。这样一来,小说的主体叙述——医生说的故事——便首先是与R市人构成互动关系,然后才传递到读者的阅读、接受行为中。
- 隐含作者——讲故事的人在叙事前有两个预设:《新聊斋》带来的虚构性和离奇性预设以及“带给趣味”的对娱乐性的预设。事实上,医生在叙述中呈现出的面貌还与所得评价相悖——劫后余生的侥幸和急于说故事的心理使得他冒失而絮叨,夹杂许多无关的议论和牢骚,离题很久才醒觉“让我说正经事情吧”。更要命的是,连他的讲述是否可靠这一点也需打上一个问号。叙述中他在在强调的“请你们相信我”,不是也正反照了言说的荒诞和不可靠?
3.第一人称内聚焦型叙事视角带来的限制性:医生的讲述中,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听众只能听到他所收集的信息,从他的描述中揣测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对其他没有讲到的方面,听众无从得知。因而小说的呈现视野就与医生的叙事导向息息相关,由他的视角呈现出的,是一个自足的拒斥外力介入的空间域,主要情节冲突聚焦于二:男子强迫医生救“人”和医生设法逃走。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重点描述了男子的“眼神”,“一对有点失神却具有神秘性的眼睛”,那双“固定不移的”,“很有力量的”眼睛。叙事者试图以“眼睛”的神秘魔力(还有男子武力上的强悍)给自己鬼使神差地留在峒中以情节上的合理性,隐含作者则试图以“转喻”方式将男子乃至故事的神秘性传递给读者,正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中豆腐铺老板谜样的微笑一样,隐含作者不直接表达对于故事的价值判断,但仍暧昧地通过转喻等符码向读者透露其所给出的立场。[^4]
上述三个方面与《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的第一人称记录式叙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在叙事层面的简洁更直接地突出了文本对“爱情”所代表的自然天性与门第观念和繁琐礼仪代表的世俗规制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前者则通过叙事层面的复杂性将文本的主题加以隐匿化和复杂化,从而使得文本在保留故事的神秘性的同时也保留了文本自身的神秘性。
从叙事节奏上看,同样如刘潇雨所言,《医生》与《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之间文本时间跨度的短与长同叙事节奏的快与慢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奇异性与叙事者的处境有关,前一个文本中的白医生刚刚脱离险境,内在的心理焦虑促使他的话语显得快与不连贯——他的目的是将自己的经历迅速表达出来,而后者则与本事的发生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这让他的叙述成为一种回忆性重构——娓娓道来的叙述心态使他在叙事时冷静、细致,这种节奏上的不同同样成为《医生》对记忆书写的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5]
总的来说,《医生》在文章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其他两篇本事相同的文章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医生》对本事刻意的传奇化、故事化重构促使它成为这一时期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一个特异性文本。
二、作为记忆书写的《医生》
普遍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带有一种浓郁的抒情性,而当这种抒情性与他的人生记忆相连接就构成了一种所谓的“情绪记忆”,孟昭兰在《普通心理学》中将这一概念定义为:“是以过去体验过的情绪或情感为内容的记忆。”[^6]刘西越在《沈从文创作中的情绪记忆研究》中指出,这种记忆是“一种基于感受力的识记,是一种以情绪、情感为对象,通过人的情感活动而实现的识记,应该谓之‘情绪识记’。而这种情绪的识记、保持、复呈,即‘情绪记忆’。”[^7]“对部分情绪与情感敏锐的作家来说,情绪与情感的识记、保持与复呈,不仅仅只是心理上的发生,它进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机制,作家的审美意识形成,作家的文学表达等方面。它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作家创作发生着作用。”[^8]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早期沈从文的创作被视为一种对自身创伤性经历的书写,这种创伤性是由他对自身乡下人身份的过度强调以及生存困境所带来的,这使得身处在城市之中的沈从文难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反而常常陷入由自卑带来的“倨傲”之中,从他在这一阶段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内心的矛盾之处。张新颖教授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提到他于1925年间受到其它学人的关照的一些事情:
“五月份,北大的丁西林介绍沈从文到创办不久的《现代评论》做收发员,收入当然微薄,但由此与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等相熟,以后在《现代评论》发表了不少作品;六月下旬,沈从文短暂离开北京去东北锦州,大哥沈云麓在那里以卖炭画教炭画为生,他去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七月即无果而返;七、八月间,林宰平介绍他在京兆尹薛笃弼的秘书室任书记,这份差事因薛即将离任而很快终止。”[^9]
后来“林宰平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为沈从文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八月,沈从文到了北京西北郊的香山。”但“他在慈幼院的生活,总体上过得并不愉快,孤单自不用说,心理上又格外敏感:总觉得自己得到这么一份工作,是一种近于恩惠的收容,因而不能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脸色。”[^10]出于这种心境,他在这一时期接连创作了《棉鞋》和《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两篇“出格”的文章,来表达他在慈幼院的复杂心态。前者“写‘我’因为穿着一双破烂的棉鞋而遭受各类人物憎嫌的眼光,更不可忍的是上司,用他手上的打狗棒敲打‘我’的鞋子;后者更是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次盛大的寿庆——夸张为三千绅士淑女欢宴的场面,其中卑微的‘他’,自感备受歧视,与周围格格不入,却对近座的女子想入非非。”[^11]而随即他就受到了慈幼院的训诫,“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13;11)即便如此,在后来写就的《呆官日记》中,他仍旧对此前在秘书室任书记的经历做了与上述两篇文章相似的写法。
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在创作初期显示出了一种对现代性都市社会的不信任和自觉的“抵制”,这种抵制出于他无法以“乡下人”的身份融入其中的现实境况,并且常常由此生发出极为负面的情绪。而值得注意的是,魏巍指出沈从文后来的回忆文字中所提到的当年“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也“从不感到消沉气馁”,这明显与当时他的真实处境有着相当程度的背离,这表明他在后来的书写中试图掩盖当年的真实。[^12]这正显示出他对当年自身的自卑有着充分的自觉。
但即便是自卑者也会诉诸一种方式来试图消除这种消极认知对自身的过度影响,正如阿德勒所言“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性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13],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看,伴随着城市书写同时出现的对于湘西世界的书写似乎就带有一种瓦解自卑、逃离现实的补正作用。而他在这一时期也确实对自己的早年经历进行了诸多重构式书写,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唤醒记忆首先具有“情感的发炎与治疗”功能。对他来说,“温习到这种‘过去’时,恰恰像在读一本属于病理学的书籍。”[^14]因而可以说,这种重构性叙述亦可被视为是他个人情感与情绪的流淌或宣泄的出口,是使情感得到平复的一种疗愈手段。正因如此,沈从文早年在湘西体验过的一切,甚至包括痛苦的一切,也在这一时段成为了他值得回忆的美妙体验。“过往经历时的情绪与事件并没有在这个当下发生改变,但新情绪的生成,令沈从文将过往所谓的痛苦回忆划分成为快乐的事,也即过往的情绪记忆在这里因为距离的缘故,成为了能够被审美,被诗化的对象。”[^15]
然而《医生》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虽然亦是对早年经历的重构性叙述,但上述的任务已经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那里得到了完成,在《医生》这个文本中,沈从文流露出来的情绪以及他对主题的重新建构已经超出了这里所论说的范畴。通过白医生的视野我们看到的是作为现代科学主义代表者的城市人对守旧痴迷于故往迷信传说的“癫子”的一种不解的冷漠。从根本上讲,白医生在山洞中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若非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他并不会遵循“癫子”的指令,这种行为似乎与他在第一次陷入昏迷前所述的“我为了病人的病,为了自己的医道,我的寂寞,谁也不曾相信有那么久那么深。我常常到街上遇见一些熟人的脸孔,我从这些脸孔上,想及那人请我为他家里人治病时如何紧张惶遽;到后人要死了他又如何悲哀,人死过一阵了他又如何善忘,我心上真有说不尽的难受。”多少有一些不和谐。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医生眼中“装作傻瓜拉我来的那个男子”,却发现他实际上并没有伤害医生,反而为他准备好了食物等基本的生存物资,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让能够医治他人的“我”帮忙看看能否救活那个已经死亡了的女子,只是他似乎由于对已逝女子的执念而陷入了一种消沉、痛苦之中。与这种完全将情感和行为赋予他人的做法相比,本应代表文明的“我”却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而将防腐剂注入她的体内,这在实质上确实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除此之外,医生的眼光之中分明显示出一种启蒙者式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在“我”的眼中,这个男子有着一双“有点失神却具有神秘性的眼睛”,在他的一系列行为后“我”也似乎看透了男子行为的目的,并对之表现出一种可理解的同情、怜悯,但医生最终的归节点却仍旧是“我若同这种人发牢骚,还是没有什么益处。”这样一种姿态与《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中的“我”位于事件之中且位于相对底层的位置有着鲜明的差异,更不用说叙事套盒外听医生讲故事的那一群各怀鬼胎的士绅老爷们了。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或多或少地从《医生》的文本中看到些批判、反讽的影子——这确实也同这一时期的其他记忆书写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那么产生这种特殊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需要从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以及当时的文坛状况方面加以考虑。
三、创作时的特殊情境
《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创作于1930年8月24日,《医生》创作于1931年4月24日,两个文本的创作时间之间仅有8个月的间隔,但文本的旨意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促使这一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似乎与这一时期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事情不无关联。
查阅相关的书信传记文献可知,自1928初从北京到达上海后,三年间影响沈从文心境的主要因素一是生活上的拮据,二是对上海文坛风气的某种不满,三是在中国公学教课后所出现的对于张兆和追求不得的痛苦。
从经济状况上看,尽管此时沈从文已经经由徐志摩、胡适的推举进入当时的中国公学担任教职,并且能够获取不少报酬,但他却仍旧不断地在为金钱发愁:1930年1月25日刚刚“得洋三百三”,两天后便不知用在何事上便耗费一空;因此王际真从美国向他汇款二百七十块钱以做补贴[^16];然而又没过多久,他又致信胡适称自己“近来因为喉部坏了,胸部发烧作咳……所有的钱还账、用、缴学费,又花光了”,请求预支一个月的薪水,以“把自己处理一下”[^17]。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即便已经不像刚到上海时需要照顾母亲和妹妹,但仍旧显得经济拮据。因此,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仍旧保持着一种高产的局面,无论是在小说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都是如此。而似乎正是担任了教职的缘故,使得他得以抽空对当时文坛的创作情况进行了一次较为完善的梳理。[^18]似乎也正是由于这一机缘巧合,使得他对上海文坛的风气表现出一种批评的态度,在7月23日写给杨南生的信中他对当时的“‘文坛’情形”不无嘲讽地写道:
“一切刊物皆无聊,求艺术深诣者所作文章,与以吃饭为目的者所作文章,相去仍不远,无聊则一。善吹如革命文学家,仍然不外想赚钱过活。名人如鲁迅,其于不相识者之忽视,以及对捧场者之特表好感,皆有可笑之事实证明。不相识则文章照例不要,熟人则不妨胡说八道,自相赞美,先生大致总有机会见到书评一类文章,你若以为那真说得公正,才真糟!上海批评家,就只会吃点心,不必花钱,用点心也就可雇定。
至于编辑,他们无人不要捧场,你若用一天功夫写成一首诗,用同样时间再写一封信对于他所编杂志说如何精彩不凡,则文章保可留用,决不退回。
书店以提倡无名作家文学号召者,当亦不乏其人。他们同情无名作家,实际是要无名作家拿钱出来买其新书。他们店中莫不雇有一批评家,而这人又不消说是瞎子,譬如来信要稿,从文把文章寄去,著自己名,在彼等便觉至少可用,若署一不见经传之姓名,马上可就退回了。……此时责任读者自然有一半。据张资平有数书,并不是其所作,但另一作者约得钱与之平分,用其名作一酒帘,此书就居然一版再版,大家发财。张资平近来固又已成为文学家而兼革命者了,他们就做这些聪明事过日子。
派别不同,则互相轻视;同流合污,则人皆天才。……若从文有一稿,一钱不要,则任何书店皆愿意马上出版,且不妨在广告上说从文真是了不得的天才。若说先拿钱,再送稿,再不然,钱货同时交休,则多数人皆烂脸走去,且另一时即借故说从文是职业作家,只要钱。”[^19]
作为浸淫于文学商业化过程中的沈从文而言,这一番话可谓是揭露出当时上海文坛的诸多不良习气,而正是由文学商业化带来的唯利是图以及他生活条件的拮据构成他对城市生活厌恶的最直接原因。这一时期的沈从文在经历了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已经不再是当年初到北京的文学青年。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自觉疏离于这些现象的态度,促使他形成了对社会更为深刻的看法;而在大学教授新文学课程以及写作课的经历也成为他在文体方面实践创新的一个重要推手。综上所述,他的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而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们看来即是他对两种创作倾向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向,其结果则是促使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诸多篇目显得更为客观冷静,也带有了一种批判的意味(《虎雏》《灯》等都是如此),《医生》文本中显示出的反讽和批判以及对于叙事方式的注重也就正好契合了这一倾向。
如果说上面的因素为《医生》在沈从文创作前期的整个记忆书写中显示出特异性的话,那么他在1930年对张兆和的求而不得以及后来在1931年年初所遭遇的一系列事件就构成《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和《医生》之间相去甚远的直接原因。
1930年2月17日,中国公学新学期开学,正是从这个学期起,沈从文开始持续不断地给张兆和写起了情书,但结果却是长期得不到回应。[^20]值得注意的是,4月26日,仅仅在《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创作完成后的三天,沈从文便寄信给王际真,信中写道:
“我在此爱上了一个并不体面的学生,好像是为了别人的聪明,我把一切做人的常态的秩序全毁了。在各方面去找那向自己解剖的机会,总似乎我能给这女人的幸福,是任何人所不能给的,我的牺牲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但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可是凡到这些事情上时,我照例是窘倒了。我的文法,到女人面前是失去效力的。我不能把言语或文字,说明我的无害于人有利于己的欲望是怎样小。女人太年青了,一个年轻人照例是不会明白男子的,我于是除了给这女人奇怪惊讶以外毫无所得。在这件事上我感到非常难过,就因为自己这弱点,凡事只抓着那近身的东西,即或明白再前面一点,有比这更完全的物件在那里,也仍然从那最近一处着手。只是看近处的近处,因此一个黑脸不甚美观的身体,也使我苦恼,从摇荡中看出自己可怜。愿意把自己放到较方便一点的地位上去总做不到,现在还是陷到这由自己掘成的井里,不能自拔。
……
我一个永远的笑话,她说的是‘不会有这件事’,从任何人看来也或者将说不会有这件事,我自己有时也不以为会有这件事,可是这事粘骨附肉,不会脱去,我将怎么样来安置自己,简直想不出另外方法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病,只有仰赖‘时间’这东西了,时间把我们地位变更,或者我会忘记这人,或者这人会爱我。”[^21]
信件可谓是真切地写出了当时他的内在心境,在此之后,他于6月30日又致信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希望她帮忙探听张兆和对他的态度,继而在7月,他基本上一心扑在与张兆和相关的事情上,但即便有胡适的出马,整件事仍然以失败告终。最终在7月18日写给王际真的信中表明自己,“因为在此事情失败,我大致无论如何应当在八月离开此地了。”[^22]
饶有意味的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的关注点正是单纯地落在了“爱情”这个关键词上:无论是三个男子如何追求女子而不得,还是最终豆腐店老板为了爱情偷尸而去都是如此。这与《清乡所见》中本事所带有的猥亵感有着相当的距离。况且,仅仅隔了三天时间便写出那样的信件,可以说信件中所表现出的心境与《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是契合的,从这个方面考虑,小说最后给人遗留下凄婉的怅惘感似乎也就得到了现实的依据。
《医生》的不同亦与作者的创作心境有着紧密的关系。1930年暑假,沈从文离开上海到武汉准备下半年在武汉大学的教学事宜。初到武汉他便获得了唤醒回忆的契机:“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大雨住处附近为一视枪场,常常试新机关枪。我住处外边,每到天明时有廿余号兵吹喇叭。”[^23]——这一切同他曾经的军队经历几乎完全一致,但在他看来这些兵却远不如“我乡下的兵”,因为“我那地方的兵,近来算湖南最有纪律最好的兵”,可以说,即便已经远离了大都会,沈从文的“城湘对立”心态仍未改变,湘西在他那里仍旧保留着纯洁性和优越性。但即便如此,他对这些底层人物还是带有同情的,他“愿意在这些中国人未来生活上有一个希望”[^24]。
可问题最终还是出现在他自己身上。“我是不会快乐,所以永远是阴暗的,灰色的。”[^25]这样的自述背后显示出他仍旧深受爱情失败的打击,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底层这种残酷现实的失望。这种低沉情绪在接下来的时间中逐渐沉淀,并且与1931年年初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相接续。
在某种意义上说,1931年对于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沈从文而言是与“死亡”相伴的一年:新年的第一天得知消息,父亲在家乡病逝,张采真在武昌被斩首示众;接下来,早年行伍间的朋友满振先在桃源被自动步枪打死;胡也频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似乎这些还不够,又加上徐志摩,“一个‘想飞’的人,给在云雾里烧毁了。”[^26](12;199)身边好友亲人接二连三的离世对沈从文本就消沉不已的心境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这似乎可以为《医生》将关注点聚焦于一场死亡提供某种程度上的解答。这篇并不被人注意的文章颠覆了前一年对同一事件的书写。正如我们在对文本形式的分析部分所提到的那样,叙事层面的复杂性将文本的主题加以隐匿化和复杂化,从而使得文本在保留故事的神秘性的同时也保留了文本自身的神秘性。将文本主题对现代世俗社会的批判讽刺与对“癫子”身上显示出的美好人性构成的冲突放置在这样一个创作背景下审视,似乎不难发现沈从文成为了一个逐渐被现代社会诸多因素拖垮了的身影——除却父亲是正常的自然死亡外,张采真、胡也频的离世均是由于一种植根于现代社会内部的因素所导致的——再加之此前恋情的完全失败与对武汉大学陈旧习气的不满,这时的沈从文似乎已经被逼上了一条绝路,正因如此,他只能搬出来自己心中的那座“希腊小庙”,以之为疲惫不堪的自己最后歇脚的地方。文本中出现的两重视角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他人对自己的不解——即沈从文将自己的身份内置到了“癫子”的身上。或许正是对现代社会的失望以及上述因素,促使他在创作完《医生》之后接连写下了《虎雏》集子中的一系列作品。
四、结语
最后涉及到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特殊的记忆书写。
在此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书写应当被放置在沈从文创作的由早期到成熟这一转变过程中进行考察。通常意义上,我们会认同沈从文的早期湘西书写背后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对于城市读者趣味的迎合,同时将之纳入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文学之中进行考虑,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走向成熟的沈从文最终超出了乡土文学和商业文学自身的所设立下的框架,显示出独特的个人风貌。魏巍认为沈从文的转变始于《阿丽丝中国游记》的第二卷,其中塑造的“仪彬的二哥”形象标志着沈从文“在直面自己的过去经历中,以当前的成绩铸就了自己的信心,成功地走出了自卑。”正是这种心态上的变动促使沈从文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写作立场。[^27]我们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在上文中提到的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于上海文坛的看法,以及文本内容从以往的自伤自怜向客观冷静地批判的转变,都标志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概括说来,此时的作品与早期创作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体现在文本正在由自发向着自觉不断深化。这种深化一方面体现为创作出发点上的转变,即由迎合市场喜好向试图摆脱商业趣味书写内心想法的转变;另一方面体现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探索,即找寻到了今后人们常说的从城市文本与湘西世界的对照中突出文化批判意识的视角,以及在创作技巧上的突破。这也正是《医生》与《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之间所呈现出的差异。显然后创作出来的前者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创作技法方面都要比后者更为深入。正因如此,《医生》不仅是沈从文记忆书写中的特殊现象,而且体现出“他的创作正在向着成熟迈进”这一现实。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七卷):小说[M].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45-67.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小说[M].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11-35.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传记[M].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302-305.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书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吴世勇.沈从文年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6]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7]肖召财.论沈从文悲剧小说的演变[D].湖南师范大学,2013.
[8]刘西越.沈从文创作中的情绪记忆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8.
[9]黄晓华.常态与癫狂的价值错位——从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看沈从文的深层意识结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1):97-100.
[10]魏巍.抵制记忆与遗忘书写——沈从文创作心理论[J].文学评论,2014,03:46-53.
[11]刘潇雨.“传奇”不奇——沈从文小说《医生》的叙事与修辞[J].中国文学研究,2014(03):85-89.
[12]闫舒琪.探究沈从文《医生》的主旨——人性的善恶、寻常与荒谬的交织[J].大众文艺,2019(03):34-35.
[^1]: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七卷): 小说[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45-67.
[^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八卷): 小说[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1-35.
[^3]: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 传记[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02-305.
[^4]: 刘潇雨.“传奇”不奇——沈从文小说《医生》的叙事与修辞[J].中国文学研究,2014 (03): 86-89.
[^5]: 刘潇雨.“传奇”不奇——沈从文小说《医生》的叙事与修辞[J].中国文学研究,2014 (03): 87.
[^6]: 孟昭兰. 普通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177.
[^7]: 刘西越. 沈从文创作中的情绪记忆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8:7.
[^8]: 刘西越. 沈从文创作中的情绪记忆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8:7-8.
[^9]: 张新颖. 沈从文的前半生 1902-1948 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54-55.
[^10]: 张新颖. 沈从文的前半生 1902-1948 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58-61.
[^11]: 同上
[^12]: 魏巍. 抵制记忆与遗忘书写——沈从文创作心理论[J]. 文学评论, 2014,03:48.
[^13]: 阿德勒. 挑战自卑[M]. 李心明, 译.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6:39.
[^14]: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 散文[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15.
[^15]: 刘西越. 沈从文创作中的情绪记忆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8:26.
[^16]: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50.
[^17]: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53.
[^18]: “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察,且得提出许多熟人大约将来说全是‘好的’不然就说全是坏的,因为通差不多。”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48.
[^19]: 吴世勇. 沈从文年谱[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93.
[^20]: 吴世勇. 沈从文年谱[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83.
[^21]: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63.
[^2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94.
[^23]: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06.
[^24]: 同上
[^25]: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 书信[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16.
[^26]: 张新颖. 沈从文的前半生 1902-1948 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20-121.
[^27]: 魏巍. 抵制记忆与遗忘书写——沈从文创作心理论[J]. 文学评论, 2014,03: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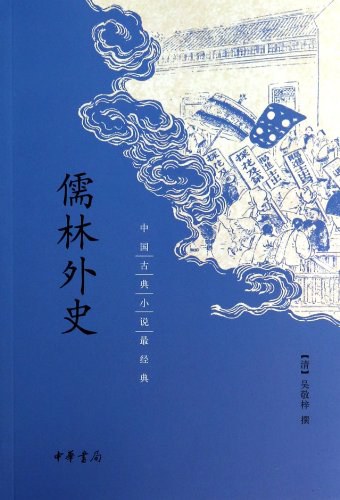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