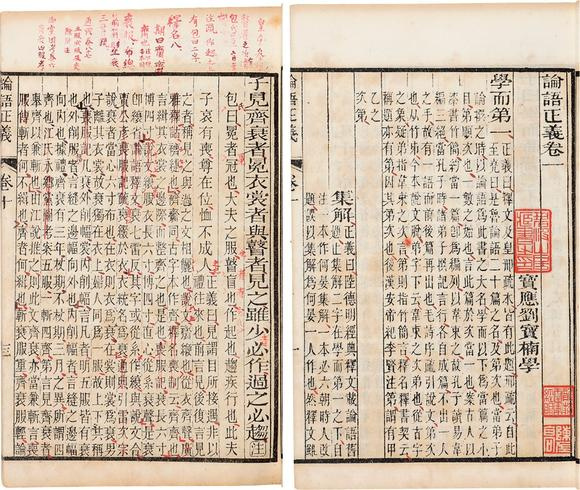从作者介入与心理谵妄谈起——读《巴黎圣母院》有感
伟大且重要的作品大概都会有一个令人无奈的通病,那即是它所蕴含的内容实在太过丰富以至于即便是汇聚了世间所有天才的笔也难以尽述它们给我们带来的体验,相对于此前读到的内容,《巴黎圣母院》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尤甚。作为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品,雨果这位令人敬仰的文豪为之赋予了极大的容量,正如米西列在《法兰西历史》中所言:“(雨果)在旧的教堂旁边建造起了一座新的教堂,像别的教堂的基础一样稳,像别的教堂的塔尖一样高。”[1]5自然,很难有人不会为卡希魔多最后那句足以令人落泪的话语而感到悲伤,也很难有人不会为弗罗洛的所作所为而咬牙切齿,然而即便对于这些都有诸多可探讨的余地,笔者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它们的讨论,因为相较而言,小说所采取的写作方式以及透过对于人物心理刻画而展现出的浪漫主义气质更能引起笔者的兴趣与思考。
小说的情节与主题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是小说最易被读者所接收的内容,而当我们透过表层的模糊感,更加深入地去观察小说的组构方式以及人物的刻画手段等这些相较而言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面,就不难发现《巴黎圣母院》确实如同那座精美而又繁复的建筑一样,有着太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一
笔者所关注到的小说的写作上的特点最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作者本人对叙事的不断介入,与题材相应的特殊的“历史笔调”,以及后来补上的完全可以看作是与故事本身并无太大关联的有关建筑艺术的文字,而正是上述三者同小说中其它艺术特点一起共同形成了《巴》颇为典型的艺术气质。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在这里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搞清楚小说叙述者和小说作者(也即雨果本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开始其实并不明显,但是透过小说中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例如在《麻烦续篇》中写到流浪儿时同自身所处时代的类比,一开篇便提出的时间节点,不断出现的有关建筑的古今对比情况,以及后来补上的三章中的大量直接的观点论述等)即可看出故事的叙述者实际上就是作者本人,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个要扼杀那个》一章中叙述者很自然地从弗罗洛的一句话展开了他对印刷术替代建筑艺术的探讨,而这些观点正同雨果本人在小说发表之后在《勘定本说明》中所言及的“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这一目的相契合。[2]3
小说的一大特点在于作者会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现身,最为普遍的情况是将读者的视野强行扭转,其目的通常是为了情节的发展或是通过视角的转换补述同一时间在另一个场景下发生的不同事件。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起到了一种情节上的衔接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扩充和完善了小说的情节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视角的切换贴近所关注的人物形成一种全知视角下的限知感(即对于作者而言是全知的,而对于他所书写的不同人物而言是限知的,而各个人物所限知的内容经过读者的逻辑层面的相互串联拼接就能够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还原出来)。例如在《夜晚逐艳的麻烦》到《麻烦续篇》这一段中,即便一直处于第三人称视角,但是所站在的角度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两次变动,即先处于格兰古瓦的跟踪视角,继而在他摔得头昏眼花之后视角转移到爱丝梅拉达和浮比斯身上,之后进入《麻烦续篇》后视点又从爱丝梅拉达和浮比斯的身上回到醒来之后的格兰古瓦身上,这样一来,尽管对于读者而言事件发生的全过程都得到了一定的把握,但是对于爱丝梅拉达、格兰古瓦而言他们各自都有一段不为对方所知的经历,这样在后来的《摔罐成亲》中故事的发展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同时,视点最终回到格兰古瓦的安排亦是为了后面描述“奇迹宫廷”的而做的准备,因为只有在新到访者看来,“奇迹宫廷”才会显露出这样的面貌。
此外,作者的现身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为了提醒读者,让他们关注一些不易注意到的内容从而得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例如作者对格兰古瓦跟踪吉卜赛姑娘时心理活动情况的描写:“她总得有个住的地方,而吉卜赛女人心肠好。——谁说得准呢?……”紧接其后他又直接跳出来提醒读者“设疑之后跟着删节号,这其中的妙想是难以言传的。”[2]77另一个事例是在格兰古瓦遇到流浪儿时,作者通过将小说中的情形与自己身处时代的现实情况相联系的方式使得读者更易于理解格兰古瓦所要面对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2]82
其次是有关小说题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小说中特殊的“历史笔调”。尽管小说的写作同传统的历史学著作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但是历史的笔法显然是可以为小说家所借鉴的,在笔者看来,刚刚提到的视角切换以及下面将要说明的对建筑艺术观点穿插都是这种“历史笔调”的体现。具体地讲,《巴》所体现出的历史性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处境、心态、社会风俗、当时巴黎城区的样貌、建筑的完备而细致的描写所共同构建起来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串入具体的时间点、历史事实与实际存在的人物来加强这样的现场感和真实性。(“正统历史的唯一一次介入,是弗兰德的御史出现在巴黎,前来为法国储君和弗兰德的玛格丽特,奥地利皇室的女儿缔结婚约。”见约翰·斯特罗克《导读》)正如斯特罗克所言:“雨果想借此为我们展示一个令人信服的场景,描绘出这一年里的各个阶层的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图卷。”[1]7他做到了,即便整部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在绝大多的层面上是虚构的结果,但是所涉及到的有关巴黎城、圣母院以及节日庆典和习俗的点点滴滴都无不蕴含着真实的成分,这种“呈弥散状分布的历史”在有代表性的态度与倾向中(即平民中的盲目迷信,非法的渎职者的森严等级,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司法的变化无常,等等)得以充分恰切地体现。[1]7而当我们将这样的写作情况同他本人所提出的观点相对照,则不难发现他也确实“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结合起来”的同时又创造出一种更加美好、更加完整的同时具有戏剧性和史诗性的小说,“它真实而又伟大、生动逼真但又富于诗意、切合实际而又具有理想,它将把司各特镶嵌在荷马的身上。”[3]6
再次是作者别有用心地对于建筑艺术观点的穿插,在笔者看来,作者在对涉及到建筑的描述时附着了他自身对于文化发展的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从小说情节本身来看,对建筑与城市状况的描述实际上与故事之间并无太多的关联,更多情况下它向读者提供的是一种背景的说明,但是作者之所以强调这在早前未能发表出来的三章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构部件,正是出于上述他的那种对于新小说、浪漫主义文学建构的观念(史诗性与戏剧性的融合),一如斯特罗克所言“一旦触及某个主题,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建筑,他就会用能想到的最广博的方式来描绘它。这部小说就像一部过去与现在同现,东方与西方交叉的浓缩了的建筑史。(学究式的余笔)”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整部小说形成了一种庞大且广博的气象,使得它在涵括高度的戏剧性与真实性的同时也具备了“荷马式的史诗气质”(即理想性与史诗性)。当然,我们不能够否定他的这种做法同自己对于建筑的极度热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通过这三章的书写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十六世纪的巴黎图卷以及圣母院的建构样式,更多地是其背后对于文化方面的深刻思考。从小说所显露观点来看,雨果实际上认为“建筑就是文化的载体,是印刷术诞生之前的人类文明的记录与见证者。”它收纳起人类文化的精华,并且成为孕育现代艺术门类的“母亲”,而当“其他艺术挣脱建筑师的枷锁,纷纷解放出来,各奔前程”之时,建筑艺术失去了从前的光辉,愈发成为一个落寞的、不再为世人所重视的老者。可以说,在小说中雨果对于建筑的过度看重不仅在于满足他个人的喜好,更多地也同当时建筑文物受到极大破坏的现实有关,他要借此来强调一种文化上对建筑艺术的重视。在这三章“无用”的文字中,作者倾其所有的才华为我们描摹出一幅又一副瑰丽绚烂的场景,正是在这些往往不被读者所重视的长篇大论中体现出了作者文学的天才以及深邃的哲思,同时也正是因此,《巴》就不再是单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畅销作品,而被赋以雨果浓厚的个人思想与艺术气质。
整体上看,作者没有选择传统的“一镜到底”式的故事叙述方式,反而采取了一种近似于现代影视艺术的剪辑方式,即将对巴黎城、圣母院的描绘、艺术史发展的观点同故事中人物成长的经历(或说人物史)的书写穿插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之中,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安排方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故事演进的节奏,但与此同时却又使得小说具有一种新意,它不仅拓宽了小说的广度同时也延展了小说的深度。从人物刻画的角度看,这样的方式在为人物性格特点的形成提供充分依据的同时又使得主要人物显得更加饱满;从小说的思想性来看,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观点的介入不但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全新的主题,同时又使它具有了超出“小说”这一文体的意义。而回过头来,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历史的拓展还是艺术哲学的论说实际上都是“作者不断跳出”的“另类表现”,它们一同形成了贯穿整部小说的一个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
二
如果说《巴》在写作方面的特色表现出作家对自己所提出的新的文学主张的践行(即对“一般化”的排斥与对文学创作自由性、创造性的强调),那么小说对于人物心理刻画时所建构起由夸张与象征组成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则鲜明地体现出浪漫主义的文学气质,笔者认为,上述的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所出现的谵妄中。
“谵妄”原指精神病科中的一种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注意力涣散、易出现幻觉,同时伴随着或亢奋、或激怒的情绪,偶尔也会出现紧张不安或迟钝等症状。[4]9在参照弗洛伊德理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谵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无意识侵夺意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侵夺的实质上是压抑机制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法国理论家克莉斯蒂娃就把非主动的谵妄现象当作一个特别话语研究,认为谵妄话语往往是政治的压抑所致,展示‘象征’和‘符号’两种力量(即政治秩序和受压抑的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5]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会产生谵妄的状态,大多是由于受到强烈的精神或心理方面刺激,而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弗罗洛在放弃解救爱丝美拉达后的失常行为:
“主教代理脸色苍白,神态失常,那样昏头昏脑,惊慌失措,胜过一群孩子在大白天放出来并追捕的一只夜鸟。他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想些什么,是否是在做梦。他时而走,时而跑,慌不择路,见到接到就钻,总隐隐觉得可怕的河滩广场在他后边紧紧追赶。”[2]397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决定不再解救爱丝美拉达对他心灵造成的巨大怆痛,直到唱诗的时候弗罗洛还寄希望于姑娘能够回心转意,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依旧是鄙视和唾弃,因而他内心中“谁也不能够得到她”的思想让他狠下心来对自己的“挚爱”做出这样的行为,这种行动标志他在肉欲之外又在杀戮与狠毒的层面同他所处的身份(神父)的分道扬镳。即便如此,作为深爱着爱丝美拉达的人,他也会为了爱人的死亡而感到无比的痛心,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就的,因而他想要逃避那个对爱丝美拉达也是对他而言的“刑场”。应当注意到的是,这里的他不似最后将爱丝美拉达交给国王爪牙时的那样决绝,相反,他还没能够在思想上完全舍弃姑娘,这同他在得知爱丝美拉达并未死亡后又重燃起情欲的焰火相呼应,然而此时正是这种尚存的希望的破灭让他突然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快步离开以及昏昏然的无意识状态正表达出他内心正在承受着剧烈的煎熬以及对于自己亲手害死爱丝美拉达这一事实的惧殚,而也正是这种痛苦显露出他内心强烈的欲望和他的心狠手辣、以及性格的复杂性。接下来他不断地奔跑“以为跑出数百公里,来到乡间,来到荒野,于是停下脚步,好像又能够呼吸了”,飞快地奔跑而忘却了实际与对身处环境的误判(“以为”)都让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弗罗洛仍旧处于极度心理紧张之中。
“他竭力想象,假如她不是吉卜赛姑娘,假如他也不是教士,假如没有浮比斯那个人,假如她能爱他,那么他在人间就能获得什么样的幸福;他想象自己也一样,完全可能过上静谧的爱情生活,如同此刻在人间随处可见的情侣:他们在橘树下,小溪边,对着落日的余晖、灿烂的星空,讲着绵绵情话;假如天从人愿,他和她本来也可以组成这样幸福的一对,他想着想着,一颗心在柔情和绝望中酥软融化了。”[2]399
这里是主教代理在绝望之后的幻想,这个时候的弗罗洛完全看清了自己,与爱丝美拉达的相遇使他心中的教义与道德被无法遏制的欲念所取代,他先是放弃了自己一生所追逐的知识与道德,继而对自己的身份表露出厌恶:认为自己和爱丝梅拉达的不幸在很大层面上是由双方的身份带来的,但实际上这是片面的。笔者认为,教士的身份本身对于弗罗洛而言是矛盾的集合,一方面,由于他是教士,因而他能够手握诸多的资源,能够达成对爱丝美拉达的陷害并且对她采取威逼利诱的态度;另一方面,教士的身份也成为锁死他一生的监牢,当欲望没有如此侵袭他的时候一切尚能被道德和知识抵御,然而当情欲的烈焰灼烧主教代理的内心,他就成为了被“宗教”这个牢笼所囚禁的犯人,无论世俗社会还是宗教教义都不允许他从“烤火架”上被释放下来,正因如此,在“撒旦带来的”情欲的折磨下他最终屈服了,他运用“上帝”授予他的智慧和借此而生的权力将自己掩藏在“神圣的光辉”之下,而当神圣堕入地狱,这样形成的结果远比本就是情欲所支配的行尸走肉要更加不堪和令人厌恶,这也正是爱丝美拉达如此唾弃弗罗洛的原因之一,亦是弗罗洛自身所显露出的悲剧性所在。
“还有一阵子,他像中了魔一般,自娱自乐,忽而想象他头一天所见的爱丝梅拉达,想她打扮得那么漂亮,欢跳活泼、无忧无虑,翩翩起舞,就跟长了翅膀一样,忽而又想象最后一天所见的爱丝梅拉达,想她只穿着衬衣,光着脚,脖子套着绳索,缓步登上绞刑架硌脚的梯阶;这两幅图景,在眼前栩栩如生,他不禁发出一声凄厉的号叫。
这场痛不欲生的风暴,震撼,摧折,扫荡他心灵中的一切,乃至连根拔除······
他就这样在田野里奔跑了一天,一直跑到黄昏,想逃避大自然,逃避生活,逃避他自己,逃避世人,逃避上帝。有时,他扑倒在地,用指甲抠麦苗;有时在荒村的街上停下来,思想痛苦得难以忍受,双手紧紧抱住脑袋,恨不得拔下来,掷到石路上摔个粉碎。
自从他丧失搭救埃及姑娘的希望和意念之后,这场风暴就一直在内心持续,没有给他的意识留下一点健全的思想,一个立得起来的念头。他的理智几乎完全摧毁,在他的头脑里僵卧了;心中只有二个清晰的形象:爱丝梅拉达和绞刑架,其余便漆黑一团。这两个形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可怕的画面,吸引住他仅余的思想和注意力,越看越以奇幻的速度扩大膨胀,一个益发显得楚楚动人,光艳夺目而又秀色可餐,而另一个则益发显得狰狞可怖;最终呈现在他眼前的,爱丝梅拉达皎若一颗明星,而绞刑架则枯若一条巨大的断臂。”[2]399、400
此处是谵妄的最突出体现,首先,弗罗洛此时已经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他想到爱丝美拉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模样实际上是无意识的行为,巨大的反差以及残酷的现实在想象中又一次给予他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无意识在驱动着他的思维不断回溯想要逃避的人和想法,同时又因为想起这些人事从而再一次促使他在行动上做出逃离的举动,因此他不断地奔跑,扑倒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然而片刻地停歇却又唤醒妄想,一环又一环地嵌套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理智几乎完全被摧毁……只有二个清晰的形象”,它们“构成一幅可怕的图画”,作者运用的喻体以及词汇总体上给人一种神秘、晦暗与可怖的感觉,无论是“风暴”(喻指绞刑)带来的昏天黑地、摧折一切的感触,“指甲抠麦苗”所带来的撕心裂肺般的鲜血淋淋与黑土相接续的画面感,“枯若一条巨大的断臂”的绞刑架所带来的窒息、衰朽和触目惊心,地狱般的钟楼、炼炉火口般的灯火、如同骷髅撞击所发出的声响无一不给人的心理添上一份巨大的压迫感,而这种心理压力正同此时弗罗洛的内心联想到自己一手造成了爱丝美拉达死亡后的颓靡痛苦,担心被发现自己是幕后主使以及来自于宗教上的堕落论所带来的惊惧相呼应。无意识的谵妄所带来的癔症正显露出弗罗洛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与此同时它又同此前格兰古瓦在奇迹宫廷被捕时的谵妄[2]90一起构建出一个由想象和夸张的象征组成的艺术世界,而这正是对《巴》浪漫主义气质最鲜明的体现。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斯特罗克,郝岩冰译,《巴黎圣母院·英文版导读》,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2】(法)雨果著,柳鸣九主编,李玉民译,《雨果文集(第八卷)·巴黎圣母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法)雨果著,柳鸣九译,《雨果论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4】杨杨,《论阎连科小说的谵妄叙事》(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9页。
【5】见童明,《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南方周末》,2012年10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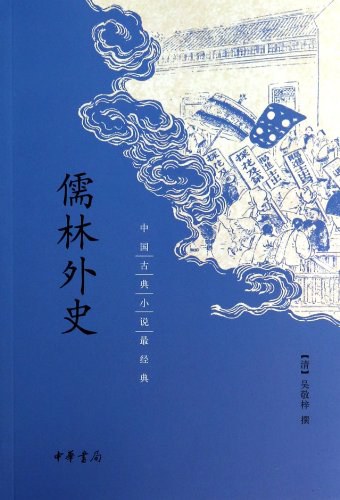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