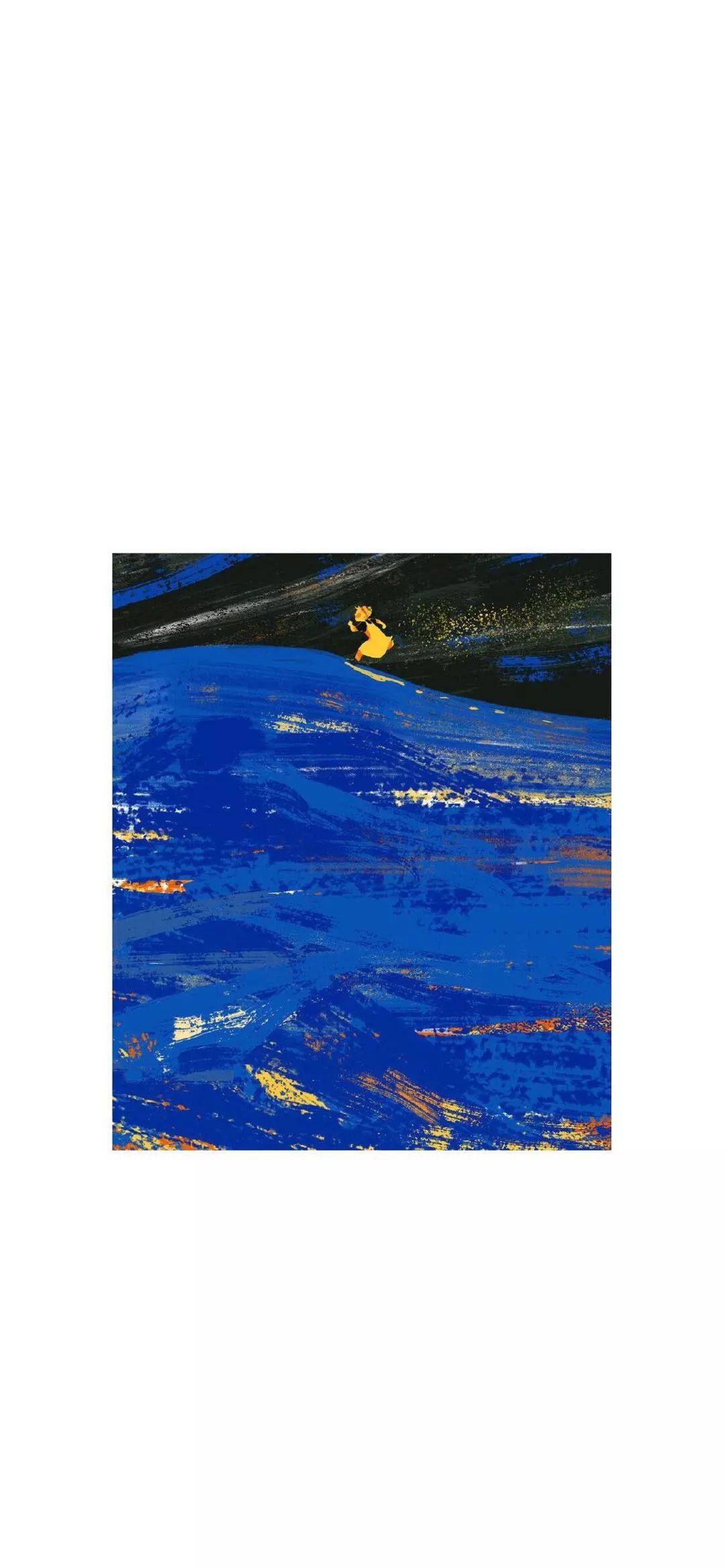我怎样陷入虚无来——一个愚人的自白
今天是假期的第104天,线上复学的第43天,大学三年级下期的第八周。
在搁笔的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一个字都没能写出来。还记得在之前的一个夜晚我试图拼凑出一些了无生趣的文字来纾解长时间家里蹲带来的极度焦虑和痛苦情绪,但在写到将近900字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删除殆尽。面对不断闪烁的键入符号和空白的word文档,我觉得自己又一次在不当的时间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我似乎十分畏惧这种失去表达能力所带来的无措感,但在另一个层面却又因为根源性的懒惰而丝毫不愿意付出什么有意识的训练。记得在阴差阳错地选上文东的钱钟书并读到他所写的一些评论性文章后,我曾一度对于能够将规范性学术书写与强烈的个人文体风格相结合的文献感到打心底里的向往。在经过称不上足够丰富的文献阅读经历之后猛地看到他那样的文章确实会或多或少受到这样一种触动。毕竟太多的文献书写已经沦为范式的不断重复和纯粹理性形式的堆砌,失去了文学本身所要求的审美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敬老师的文字就有多么富于文学性,但它至少做到了独具特色。那段时间我甚至试图思考如何将文学性与自己不足观的学术垃圾相结合,不过最后仍旧是不了了之。
大一下学期刚起步的时候,我提到这个公众号的主要或说唯一作用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理解自己,但当第二个年头也悄然逝去,我却还是在不断原地踏步。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转变了自己的生活重心,试图去追求这个世界上本不应强求的东西,随之而来不断的滑铁卢让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面对时常处于崩溃边缘的自己,我毅然决然地背叛了曾经天真的想法,抛弃了当年定下的但现在看来幼稚不已的设想,转而将公众号视为纯粹个人记录的工具。这种态度的转变后来逐渐拓展到对朋友圈的管理以及如今经常用的豆瓣上。转变所伴随的心境无疑是复杂的,但占大头的原因自然是出于自陷于“得不到爱”的苦闷之中不能自拔从而连带的多种消沉情绪,可以说这种情绪伴随我走过了20岁这一整年,结果自然是又一次辜负了曾经的自己所作出的期盼。
在去年一整年的大量交流和自发性叙述中,我逐渐建构起“因为韩少功的挂科从而让自己又一次陷入颓靡”这样一套说辞。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功经过长时间的不断重复而成为自己不断逃避的潜意识观念,在不断的述说过程中我逐渐耽溺于这样一个自我构建的话语体系以致长时间地回避更为根本的问题。这种相似经历在短短数年间的再度复现本应使我保持高度的警觉,但很显然,在又一次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当年一致的做法,并因此长时间地沉溺在自我开脱与沾沾自喜中而毫不自知。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这一年的诸多事件,我逐渐看清了围绕着“爱情”这样一个注定通向虚无的命题所展开的一些问题。
需要承认的是,对爱情问题的书写是有必要的,不过我一直在回避这样一种在自己看来过于直露的书写,反而采用稍带文学性的文字表述特定时段所产生的极端情绪,因而在去年一整年的书写中才有了那么多次以“8”为题的且现在看来有些可笑的虚构性文字。长时间进行这样书写的结果是越发缺乏理性判断,从而不断沦为自己感性的奴隶,也就是深陷恶性循环之中进行自我感动而无法自拔。也正因如此,我的书写出现了较强的割裂性:一方面在论文写作时运用近乎定式的组构方式进行纯理性论证,另一方面在随笔中完全任由情绪流动进行具有一定跳跃性纯感性抒情,文体上的割裂在现实中通过写作时间的割裂得到了加深——前半学期的纯感性叙事在后半学期论文的重压下几乎无暇得以展开,正因如此在进入假期后对论文书写的疲倦致使久久不愿动笔,而感性的书写又难以找到曾经的运笔感受,这就成为文章难产的重要原因。
到现在为止我不敢说对自己对此有多么深的了解,但在某些问题上确实得到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使我逐渐对些问题得到了最为粗浅的解答。
在一次又一次追求他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对爱情的定义,并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它之间的距离,因而形成了现在的观念,即对我个人而言它并非可求得的,只能等待毫不可靠的“不期而遇”。出于这种认知,我发现长时间关注这一问题是极为不可取的态度,因而现在的自己逐渐放弃对爱情的妄想并开始设想自己独自生活到老的未来。自然,在这样的过程中,理想的情况是让自己保留对“爱情”期待,使它成为一种内在性想法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毕竟能够寻求到精神伴侣的可能性基本是微乎其微,在无法满足于日常交流与性需求这样简单层次关系的情况下,似乎只有这样是目前最适合自己的选项。
伴随着对于爱情问题的确认,我也愈发认同原生家庭对个人成长和性格构建的重要意义。冬天跟白羽大佬她们一起从奇异果回寝室的时候我们偶然谈到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同通过对他人的初印象就能够或多或少判断出对方的成长环境。由于认同个人性情与成长环境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并且幼年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铭入骨髓的影响。基于这种观点,每个个体的基本性情被我认定为是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换言之,内向悲观性格和外向开朗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逆转性,看似的转变本身往往发生在外在表象而难以触及根本内核。
可以说正是对上述观念的确认,让我愈发坚定个人本位主义的想法,也愈发厌恶他人对我进行挑三拣四的行为。连带的结果是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更加能够看清自己真正的样态(当然这很到程度上还要感谢我身边的好朋友们),这让我感到自己越发真实而非如同以往那样多少带有想要隐匿自我的想法,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持下,我删除了那些曾经自以为十分珍视但却在对方眼中毫无价值的人(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行为在为自己带来遗憾的同时也缓解了自己一直紧绷的神经。
在处理所谓的“爱情”问题的过程中同样促成了自我对于“友情”的重新审视。当网络联络者又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宣告双方在“爱情”方面的不可能时,提出拒绝的一方往往会表现出一种“试图补救”的姿态——他or她会提出所谓的“做朋友吧”这样一种提议,以此来短暂安慰自己拒绝对方后为自身所带来的“愧疚感”。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看似友好的表态实际上有着极为自私的内核:一方面对方通过这样的表态试图维护自己的友善身份,另一方面又将“朋友”这个能指本身的所指完全地践踏了。尽管上述内容在提出者那里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但正是这种下意识深刻地体现出当代个体在面对情感问题时的自私性。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目的并非为了强调提出拒绝的一方是有多么令人厌恶,相反,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促使笔者个人当下更愿意将一切情感问题视为是从个体从自身意愿出发,以个人利益的实现为最终目的的一种现实的活动。对此,作为正常人的我们实际上并不应当也毫无权利做出任何意义上的是非判断。但应当从中习得的是,从观念上试图避免和遏制这样一种仅存在于最为肤浅的表层的“伪善”。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上述的反思似乎正是由于对于不断追寻这件虚无缥缈之事感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厌倦,它所消耗的是自己原本拥有的纯善和寥寥无几的朝气,不过到现在来看,这种朝气几乎已被消耗殆尽,即便对于性的官能渴望仍旧潮起潮落般冲蚀着自己的内心,但缺乏内在精神交流的官能满足永远如“欲壑难填”一词所言一样——显得空洞且无趣。况且在当今时代,圈子内部对于官能体验的庸俗化日益加剧,由此所带来的难以餍足感只会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破除守备而愈涨愈烈,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愈发混乱的交媾现象和自身污名化难以去除等问题。当然,笔者并非意图表现自己有多么清高,作为最平凡的普通人的我,自然也难以逃离上述的境况,但或多或少地思考确实对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疏离这样称不上合适的现象有着帮助,也不会再如同少时那样人云亦云。
愈发偏题了,现在重新回到对自身的疏理上来。
仅有粗浅了解与缺乏深度阅读让我知悉自己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免显得片面和主观,并由此了解到注定已有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对这些问题发表过深入人心的见解。但这样并不会让我个人感觉到这样一种自我疏理是无意义的,通过三年对于文学文本的研究,笔者深知先行细读与先行阅览文献两种方式所产生的对于文本的把握程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所唤起的是一个后发印证的过程,这种印证带来的正反馈远大于后者,笔者这里所做的事情也有着近似的道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刻意回避社会热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对于绝大多数的社会热点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距离——可以说仅仅知悉有这样一件事情的存在而对内在发生的情况毫不知情。这种刻意回避尽管加速了自身朝气的消失,却让自己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一种“不轻易发声”的态度。“对并不了解且没有把握的事项永远不要轻易发声”与“我所知道的仅是自己一无所知”这种想法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暗示,已经被深深印刻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学术训练带给自己的理性和要求对问题有深度的理解这样一种标准似乎是使大多数人文科学研究者远离当代事件的原因。如果在外人的眼光下看去,这样的行为就显示出一种表面上的“麻木不仁”,近期方方事件中知识分子的集体失声似乎正是对此极为贴切的一种展露。但事实是,问题似乎不应当被如此轻易地提出和回应。社会事件背后的深刻思想文化背景让绝大多数人的发声显得粗浅和武断,而学术研究的要求是沉潜,细致地思考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将之放置在整个学术背景和社会精神文化状态之上作出细致精深的解剖,这在当代无疑是一种难以跟随信息社会瞬息万变的举措。或许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学术界尚未开始便已在社会舆论中失去了时效性,亦或许出于某种众所周知原因,深入客观的纯粹学术探讨也会演化成一种“不可能”。这样看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是否已经与当代社会的现实实践形成了一种难以弥缝的鸿沟?在笔者看来这似乎是可能的,当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放弃对当下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解读而转向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样一种事实便已经成立了;只是同时出于对当代学界认知的粗浅性,笔者又无法不对自身的论断表现出深深地质疑。
如果说对于人际关系的悲观认知和对社会现实的刻意远离尚未铸就通往虚无的道路,那么现实的的苦闷和对自身行为意义的质疑则成为将自己逼上这条路径的直接原因。
随着年纪的增长,愈发发现自己与原生家庭之间有着难以缝合的根本性的观念差异,而对人生的过度片面、缺乏眼光的规划构成了没有退路的现实,当自身对实现经济独立并完全脱离家庭生活有着强烈的执念却又在现阶段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这样的现实之间构成一种难以处理的矛盾时,陷入愧疚和自责就不再是什么笑谈。另一方面,在自己所意欲投身的志业中遇到完全未曾想过的困境,并对“不断进行的文献书写是真的存在任何意义”产生难以抹除的质疑时,陷入虚无反而成为更加合情合理的反应。
三月的时候,自己在群里与同学用尽百般方式讥讽沈从文早年的文章,那时自己从未想过在愈发深入了解他之后能够从中获得极为深刻的共鸣。早先的自己在面对这种无可否认的共鸣时表现出一种不愿相信事实的逃避态度,直到阅读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逐渐理解自身之前行为的可笑,继而放下所有防备接受了这样讽刺的现实。现在看来,当时自己对他的奚落和批判无疑可以完全照搬到自己的身上。当然,沈所在的时代和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异,促使我产生苦闷和虚无的根本原因也与之相去甚远,即便如此,却也仍旧无法否认共通性这一现实。相较而言,当年的他最起码还有着能够正视自己的态度,想到自己却连如此也不如,又何来的资格去嘲弄年轻时的他呢?
仅有一面之缘的兆丰学长前一段时间在空间发了一篇《论文小感》,里面写道:
两年后,我明白,做论文之前,是需要做一番文献综述的,看一看前人在这个领域做过什么研究——如果和前人做的研究重复了,你的研究便没有意义。到了这时候,我才从翟天临式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学院派规训的学者,大约知道了学术规范为何物,可晚慧的我此时已经大三了……我打开知网,看前人的论文,却发现也遍是重复。文学研究,原来十有八九,都没有意义。如此看来,自己再继续做些对文学本身没有意义,却对自己毕业有些意义的论文,似乎也并非不道德的。
可人一旦知道自己的做法不道德,道德感就会让人白白受苦。于是几年来,我也都在所谓学术的痛苦中,并非是因为此事本身辛苦,而是因为知道自己无论做多或者多少,都是白白地做而已。做的论文,对自己有意义,而对文学,或者时代、世界无意义,也会消解自己存在的意义。
呜呼,论文做着做着,人变成了虚无主义者。如今还在继续做论文,赶论文。引用、脚注、文献综述,做得十分娴熟。几百字,上千言,拍脑门的想法少了,灵气、真实的思想,却也少了。又做了一千言,脚注又增加四五条,多么漂亮的论文,却只觉得是自己思想的死胎。
本科时代的论文,坦坦荡荡的A,不带减号,已经是毕业论文。如此看来多有反讽,因为这不仅象征着本科的毕业,似乎还象征着基本学术训练的毕业。本来,从此可以坦坦荡荡做人,但研究生的论文,变本加厉地走过来了,绑架着我,让我在虚无里,老老实实待着,暂时不要出声。在虚无里,我有时又会想到高中做练习册抄答案的生涯,觉得自己相较于当时,还更加衰弱了。
这正说出了我的感受。在家的这段时间深切体会到自身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游民属性,围绕着上面写到的诸多问题天天生发些可有可无的牢骚,即便信誓旦旦准备考研,但到如今却也连abandon都没有背得下来,文学史也早已忘却殆尽,浑浑噩噩至目下,又遇到那样成堆的毫无意义的论文作业积在面前,想要休学去逃避却又惧惮得到一个“啃老”的不雅名号、惧惮脱离了同代人的人生,现在看来唯有遁入虚无才能保留的一点点的生存意义,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想到这些那些有的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