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作业二题
一、阅读沈从文与鲁迅的作品,两位作家各自任选一部(小说或散文均可),对比二者的异同,谈谈你的理解。
《狂人日记》与《山鬼》对读:
从风格来看,《狂人日记》的书写笔调显然是典型鲁迅式的冷峻严肃,甚至给人以压抑和恐惧的感受;而《山鬼》则截然相反,它充满着健康清新的色调,整体的叙述也是淳朴自然的,占据绝大多数篇幅的书写近乎一种桃源式的幻想,直到最末伍孃的细想才带入了一丝隐忧。从这个角度看,它们分别体现了两个作家最典型的创作风格。
值得关注的是两位作家所塑造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疯癫形象。
首先,二人疯癫的性质有所差异。狂人的疯癫如其所述体现为陷入“迫害妄想”,从根本上讲是由外部世界引起的,由于这种癔症现象的出现这种疯癫有很大可能是病理性的;而癫子则截然不同,他的疯癫只是在外人看来如此,小说中并没有明确他究竟有何种病理性诱因,并且这种疯癫实际上只是与当地传统百姓有所不同,换言之,他并非真的疯了,只是由于自己的言行与他人有着较大差异以致外人难以理解因而被视为疯癫。仅从表象上看,癫子更像是陷入一种痴的情况,但这种痴是有限度的,因为他还懂得处理人际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癫是自发性的心理因素导致的。
其次,周围人对待疯癫者的态度有所不同。在《狂人日记》中,所有人都对狂人敬而远之,他们以一种审视病态的眼光看待狂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毫不相干的外人都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狂人在疯癫中所说的话都是惊世骇俗的,但他们对待这些一语中的的论调却始终保持敷衍的态度。在小说中,狂人本身以及“正常”的人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前者代表苏醒过来的人,亦即“铁屋中的醒者”,而后者则象征封建传统腐朽破败的世俗礼教维护者,他们占据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而狂人所经受的正是沉默的大多数正在进行的“无声中的吃人”。因而从本质上讲,狂人与外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人性在经受着封建社会道德的残害。在这种主题下,鲁迅通过深刻尖锐而又冷峻压抑的书写让这种令人抓狂窒息的感觉烘衬了出来。《山鬼》则截然相反,癫子与外人的关系无疑是融洽和谐的,甚至前者在后者那里是可爱的受欢迎的存在。沈从文在小说中书写的风俗和人物都有着健康淳朴、清新善良的面貌,以伍孃为代表的劳动者更给人以自立自强的印象,尽管他们保留了传统封建迷信,但同时带有的那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却又更显得熠熠生辉。笔者认为,这种处理体现出沈从文与鲁迅对乡民的不同态度。相较于批判封建文化,沈从文似乎更关注对美好健康人性的赞美。如果说《山鬼》中的一般人物已带有这种健康人性,那么癫子身上所体现出的则更胜一筹,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喜爱他并担心他。如果将被视为发癫的行为列举出来,那么可以发现,癫子大多数疯癫的举措只是为了寻求某种心理的满足,无论是走上老远去看戏还是看桃花都是对美好事物的可理解反映。在这个意义上村民的态度就成为一种比对,他们将这些行为视为是癫,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自足愚昧是未开化的体现。笔者认为癫子身上的特质有带有现代人的敏感特质,他在追求美的过程中得到审美愉悦同时也为某些事情感到伤感,这种情绪在伍孃这些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因而小说在这个角度上可被视为体现了一种启蒙话语,但相较于鲁迅式的直接冷峻,沈从文这里无疑显得更加温和也更为含蓄。
二、如何看待沈从文1940年代小说中的爱欲书写?对比沈从文1920-1940爱欲书写四十年代的不同?
沈从文的爱欲书写正如解志熙教授所言是从未中断过的,无论是二十年代的大量自叙传式创作,还是三十年代中不断出现的批判讽刺城市的作品以及诸多湘西篇章,情爱和欲望两个关键词从未离开他笔下创制出的文字,前者如《篁君日记》《呆官日记》一类的对自身渴慕与女子相恋或受相思猜忌而矛盾不已的大量心理叙事,后者如《八骏图》中对达士先生的嘲讽以及《月下小景》《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之类的湘西爱欲传奇。可以说,沈从文长久以来不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书写自身对爱欲的种种态度,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沈从文似乎陷入了一种高度性压抑带来的病态性心理。
如果将他早年在湘西的军旅生涯与进入城市后所长期忍受的压抑生存方式并列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判断实际上是可考的。湘西社会对自然天性的无拘无束本来应当构成沈从文爱欲观念的根本底色,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不仅在他创作的《丈夫》《柏子》《采蕨》等篇目对这样一种顺遂天性的男女关系有所展露,在《从文自传》中他也写到了相关的船夫如何去找妓女、清乡的士兵如何与当地妇女产生关系诸如此类的现实。然而这种本有的对于男女关系顺遂天性的认识却在他今后的人生中一次次被打破,换言之,尽管他仍旧保留着这种爱欲观念的底色,但却在今后人生遭遇的诸多事件中不得不一次次将这种观念悬置,甚至被迫接受它的“不可能实现”。
沈从文的初恋对他整个人生的情感道路而言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由于钱财被悉数骗去,让他甚至自觉在湘西已经呆不下去,更愧对于母亲,这是促使他出走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场恋情对沈从文而言应当是极为重要的,初恋对于沈从文个人爱情观念的形塑作用应当得到重视。自此开始,沈从文的爱情道路正可谓是饱经摧残、停滞不前。当贫寒得只能瑟缩在窄而霉小斋的沈从文不断为“食”苦恼不已时,情欲同样不断裹挟着这位内向、自卑的青年。《怯汉》中尾随女子的那个男子,《呆官日记》中那个不断纠结如何对待女同事并怀有某种自得又显得患得患失的男子都是这一时期沈从文个人状态的生动写照。这时的沈从文作为一个刚刚进城的“乡下人”,由于身份的卑微(与大学生相比)与财务的困窘陷入了极为艰难的生存困境之中。然而正值青年的他却又无法抑制情欲的焰火,一次又一次地上街尾随、盯视女子,因而这样一种“高攀不起”带来的情感层面的创伤性经历就构成了沈从文悬置顺遂天性的爱欲观念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种只能远观,连接近都不敢想象的自卑使得沈从文的爱欲只能通过诉诸笔端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持续不断地自我暴露和心理剖析在客观上会强化已有的认知,从而促使沈从文此时所长期无法摆脱的性压抑内化为一种潜在观念。因而,由“不得”而生发出的渴望,就成为了沈从文此时爱欲书写中所展现出的那种病态特点。这种病态性在他追求张兆和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身为教师的沈从文即便再怎么富于自由主义观念也不应当做出追求学生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举动,更何况沈从文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种“胁迫式”的做法,张兆和在当时的日记中所记录下的文字清楚地显示出她对沈从文狂热到以至丧失理智般的热情有着一定的犹疑,她不能理解对方为何会对自己痴迷到如此境界,因而在反感的同时或多或少地显露出一种同情。从这个角度看,这似乎正对后来他更为“病态”的性心理的提供了一种暗示。
都市生活带来的生存困境促使爱欲困境长期处于病态的压抑之中,这使得沈从文即想要得到情爱却又根本无法得到它,文学创作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纾解这种苦闷的方式。当都市书写构成他个体经历的重现时,顺遂天性的爱欲观念则通过湘西书写加以流露,无论是柏子、阿黑还是偷尸的豆腐铺老板,他们都被塑造为富于人性美的角色,并被置于称赞的位置上加以推崇。但无论是发生在阿黑身上的野合还是发生在豆腐铺老板身上的偷尸都显得有些不那么正常,尤其是后者更为突出地体现了沈从文对于情爱的极端态度,这与都市书写中叙事者对女性人物充满性意味“凝视”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沈从文的爱欲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他自己个人对于男女情爱的追求,而这种态度由于早年情感的创伤性经历影响,显然带有了一种病态性特征。这种病态的性心理内化为了沈从文的潜意识,一再地通过文本展现出来。而当某个突发性经历将这种压抑的欲望唤醒时,作为作者的沈从文就会更进一步将之付诸笔端。
这里,笔者仍旧认同解志熙的观点,即随着生存困境的解决,沈从文通过“情绪的体操”这样一种创作理论,逐渐将自己的情欲书写内敛化,以讽刺和抒情的面貌展露在世人面前。而当他偶遇激起自身情欲激情的事情时,他身上所特有的强烈倾诉欲就促使他将这些事件和这些情欲诉诸笔端,这也就成为了他在四十年代重返爱欲书写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正是这种自我暴露的做法成为了他病态性心理的延续。如果说《梦与现实》还相对含蓄委婉且与早年的自叙性书写有所相似的话,那么《看虹录》《摘星录》中令人难受的男性凝视视角则确实有着“近淫”的猎奇特质,尤其是后者直露地性书写更是暴露了沈从文个人的恋足癖(这是基于《摘星录》确实是根据他个人经历所写就的这样一种假设而做出的推论)。根据弗洛伊德理论,恋足癖等性癖好正可被视为是早年创伤性经历在人内在精神层面留下印记的证据。这样一来,不难看出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的爱欲书写其实与二十年代的爱欲书写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而其背后的相关爱欲观念则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的不同则在于,后者是一种更为有意的建构,尽管笔者认为他所谓的玄之又玄“生命”诸说更多起到的是欲盖弥彰的效果,但不能否认的是,他所做出的这样一种试图接榫的努力恰好证明了他想要赋予爱欲书写以更为深刻的内涵这样一种考量。而考究他的人生经历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沈从文确实处在一种不断地变动和思考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抗战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或许是湘西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难以前进的困境的缘故。但无论究竟是何种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选择在四十年代重回爱欲书写必不是一种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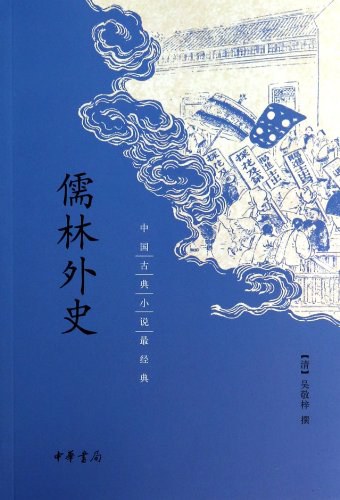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