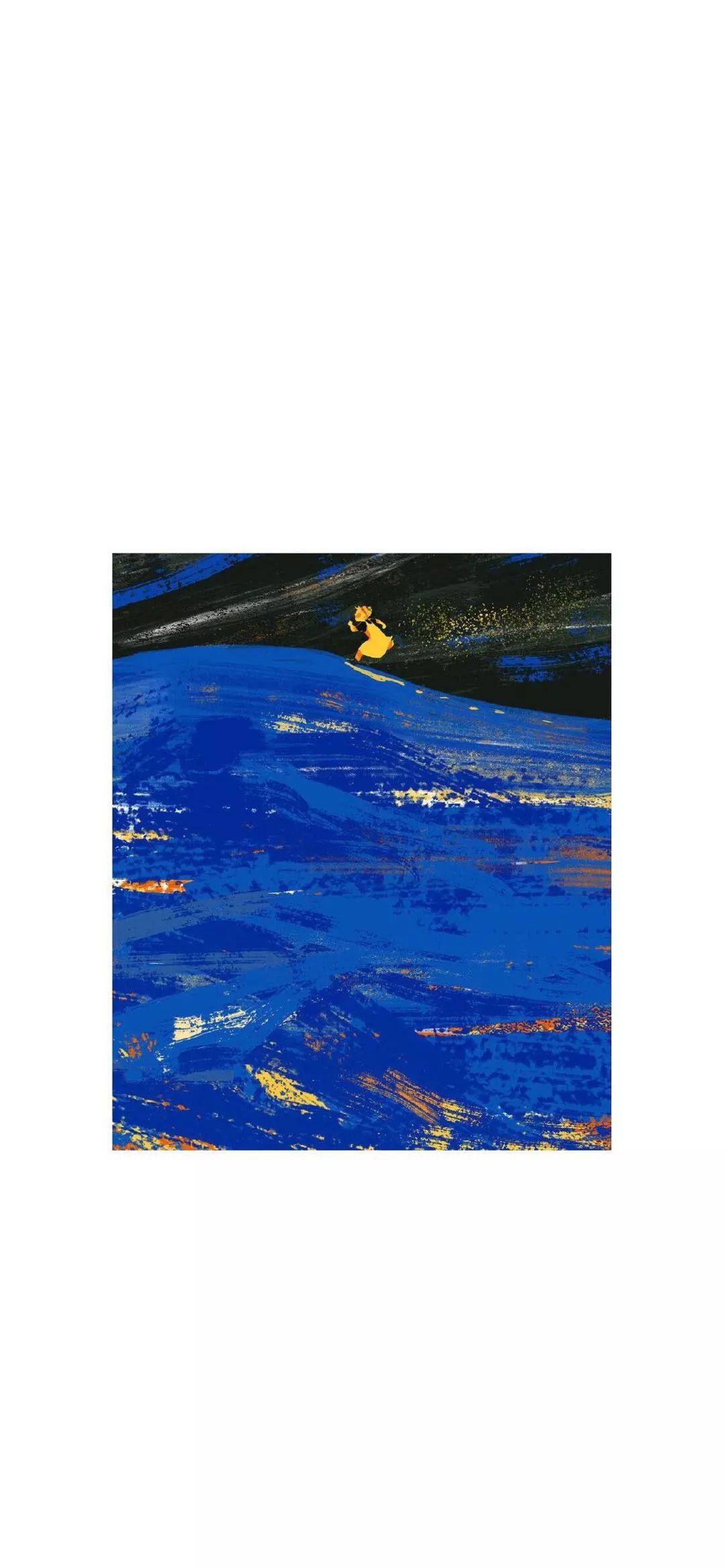杂思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阴暗的光露怯般照进一隅,百无聊赖随窗帘摆动,增增减减它占据那块瓷砖的面积。
按掉闹钟后又过了多久?安静得能听到从阳台传来车流奔逐的声音。下意识里,翻身、蜷缩、拉紧空调被、塞好嘴角,眼睛还是不愿睁开。
一般来说,一天中最美妙的时间便是与睡眠相关的头尾两端,心情平静、有惬意清爽的风吹、不用考虑日日月月年年上演的糟心事。虽然都只有短短几分钟,但还是令人感到莫名心安,好像挨到那个时间,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了。
有想过一觉不醒会怎么样吗?
这个问题太俗了,也确实没想过。想的从来只有“要是能一觉不醒就好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后果如何。太麻烦了吧,还要考虑死后世界是什么样子,想要结束此生不就是为了摆脱活着永远也摆脱不了的麻烦吗?为什么死前还要给自己找这么个麻烦?
这么说也有些道理。
“手抓饼在厨房,拿出来的时候记得拿吸油纸擦一下电饼铛,然后盖住放好。”
很久没看到那个小本子,她把“铛”字写错了,这个小本子里她写错的字太多了。迷瞪着还有些站不稳的时候,没想到脑海里浮现的是这些想法。
餐桌紧靠客厅那堵阻挡对流的白墙,风吹不过来了。往后靠一点,到两间卧室门中间,还有凉气。但不能坐在那里吃饭。
时间过去太久,手抓饼从焦变皮,跟啃皮鞋一样难咬。每次涂番茄酱的时候都想着要去买一个方便抹均匀的餐刀,但从来都没有付诸行动。蕃茄酱一点也不均匀地粘在手抓饼里,一口一口,跟手游抽卡一样,概略不一。
又是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一天。
下着雨却没有风,凉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散。“雨下不透还不如不下。”脑海里又想起她从小念叨到大的话。或许这就是摆脱不了的血缘关系,一点一滴,以为不会相似的地方随着时间流逝、生命的增长,渐渐浮现出来,狠狠重击心底可笑的自信。越来越像了。跟他还有她,那些曾经他们身上被我厌恶的地方、想着永远也不可能会沾染上的习气,正开始越来越多、原封不动地浮现出来,那份斤斤计较、那份懒惰、那份过于刻意的刻薄。他们施以我的,我也开始施以他们,他们施以彼此的,也追着我不放。
不怎么会想到要一跃而下。死亡最好还是选择不那么痛苦的方式,毕竟走向死亡本身就是因为活着的痛苦。或许,有意义的死亡要基于坚定的信念,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否则,与其称之为死亡,不如说是意外,那便是妥妥的悲剧,对于别人也对于自己。活着本身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有些人自知,有些人不自知;有些人知道的清楚一些,有些人只是朦朦胧胧意识得到;不是读书多的人就一定了解更深,也不是饱经沧桑的人便可以有过来人的优越。或许意识得到的人便对痛楚更敏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痛苦要比别人更深重;或许意识不到的人一旦觉醒,所承受的要更加令人难以预料。只是,从最浅显的层面上看去,敏感者在生活中所受的影响要更大些,麻木者如字面意思一样较少受到影响。这话说的有狡辩开脱之嫌。
药时断时续,想起来的时候吃一颗,想不起来就停下。习惯于欺骗,可能也就因此觉得自己好了。如果能将自我麻醉的能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就好了。
真正脱离那个环境的时候,确实是能有一些效果的,但痛苦永远守恒,现在我得以了解,但这是后话了。
或许是因为变胖了,对温度的感知也更加敏感。烦躁总是与热结伴袭来。我却又是怕冷的人,也并不习惯对着空调吹,每当这样,结果不外乎很快感冒,夏日的重感冒令人无比痛苦,因此至今我还对那年郑大的空调记忆犹新。这么看来季风性气候对我从来都不怎么友好,但我却没办法改变。早早打开空调,然后躺在远离空调的沙发上成为居家时的常态。不过现在,这也成为过去式了,我仍旧十分眷恋,也只能眷恋。
人的思维正在随着他所从事的事业与选择的专业不断分化,因而理解,随着年岁的增长也逐渐变得困难。简单粗暴的做法是攻击,奉自己的视角为尊建构所谓的“鄙视链”,这多少显得有些无知得可悲。忘了是梁森老师还是蓝旭老师在一次课上笑着说在坐的大家也算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文语境,这个称呼或许难能可贵地继续保持着中性,但却不时显露出向“傲慢”滑动的倾向,如果的确如此,这或许是这个词语在白话文运动以来第二次走向贬义。希望这不会成真。敬老师无数次在课堂上宣告:“我们的语言正变得无比粗鄙。”李厚晨也不止一次在翻转电台里表示当今的我们已经丧失了好好说话的能力。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些判断很可能被认为是傲慢的,究其原因,这种傲慢很可能会被归咎于说话者自身的身份。这样看来,我们本不愿陷入无止境的身份对立之中,但实际身份的划分早已开始,并且我们已经不自觉地进入其中。就像有的人分析的那样,西方的身份政治将社会人群纵向切分,马克思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则是将人群横向切分,而在当今的社会里,切分很可能更为复杂,毕竟,特殊性同样于此存在,在横向与纵向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人群的身份将更加明确,对立带来的攻击性也可能更加激烈。
我对这个社会的现实并没有深入了解,也不清楚所谓的“广大人民群众”究竟生活得怎么样(如果我和我的家人仍旧没被抛出这个范畴的话,或许还是有些发言权),并且对于专业的社会学分析也一窍不通。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不去说话,也尝试规避很多社会议题,但问题在于,随着年岁的增长,一部分社会议题已经不再是可以逃避的,甚至它直接变本加厉地贴在你脸上,让你不得不正视并应对它,因而那种噤声的态度或许正在变得不合时宜,毕竟,在这种时刻,逃避本身就有可能是在作恶。
当互联网日益发展为现代人的体外“器官”,它身上发生事情都会或多或少牵动不同的个体,在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既然的当下,关注互联网舆论在也就或多或少带有为自身“诊疗”的意义。了解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发展情况的人都知道,贴标签有时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清晰明确,相反会造成更深的遮蔽。但是当今的舆论与语境,正有向这里转变的倾向,如果用更简单的方式讲,“大字报”。
现在回头看去,中文的词汇确实正在经历一轮新的“清洗”,梳理“文艺青年”、“公知”等称呼的词性流变历程,或许就能更清晰地看出这一倾向。本质上,我还是持以温和的改良主义,原本我一直十分厌倦儒家的“中庸”思想,但实际上作为中国人,确实很难逃离这一成见。激进的革命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必然同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与儒学的一边倒式反拨脱离不了干系,在历史语言的修缮下,这种理念一方面被高高奉于庙堂、定于一尊,另一方面却又被无限打压,失却了“春风吹又生”的可能,这种由现象抽离出来的形而上的背反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着,或许就是构成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大根源。但是即便是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尚且还有学衡派的持中之论,而如今,经过无数次对文学史“重写”之后,对学衡派早已经过由贬抑到客观持中再到如今所宣称的“具有先见性”。这样看来,持“中庸”观点不应该被简单视作是“和事佬”、“和稀泥”选项,也不能宣称持论者的“迂腐”和缺乏改革意识。但现实却是,“中庸”往往在舆论场中处于双边倾轧的地位。“二极管”一词虽然形象贴切,但本质上仍旧跟刚刚提到的贴标签是一丘之貉,由此得出的结果往往是被简单化了的(这里是贬义)。最突出的便是与女性主义相关或是与粉丝文化相关的社会事件。但我之所以会对“二极管”深有感触,则是因为一些游戏的舆论场中此种现象的频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感受到议题的不可避免。实际上,这种简单化正是阻止议题深入的重要原因,舆论浮于表面且通过持续不断地“标签化”(泛化)延续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本质上是在消解个体的特殊性,也即消解主体性。我们都知道,主体性的建构是西方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结果,也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之一,尽管后现代主义不断批判反思启蒙,但本质上他们仍旧以被建立起的个体为原则,是不断反思如何在现代社会的情况下解救不断消解中的主体性,所以福柯选择再“启蒙”,所以哈贝马斯提出用“主体间性”来置换“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离不开人民主体性的建构,但这实际又同现有的社会教育和“主流思想”构成冲突,因而上述现象的一再发生,并且逐渐成为社会奇观就不能说与这种矛盾的思想发展状况毫无关系。
消费社会本身具有消解深度的特征,当中国逐步步入这一具有后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环节,如何处理思想上的滞后与物质上的高度先进便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主要矛盾的不断更新和调整,实际上就是在说明这个问题。只不过在绝大多数人眼里,这只是由一堆无甚意义也有些让人不知所云的汉字符号构成的句行罢了。说到这里,我其实很好奇当年这句话变更时,那些积极转发的众多人中,有多少是真正理解它的,又有多少只是一时跟风的。换个角度想,这是否又表明了跟风现象本身就是“意料之中”与“被刻意利用、建构的”呢?看起来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实际上,这里的“跟风”现象也与当代互联网舆论场里乃至更远年代里那些“跟风”并没有多少区别。
本质上,“跟风”是一种非理智行为,它缺乏个体的思考,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并且也是在将复杂事情简单化甚至无脑化,在这方面,它与“标签化”是一致的。或许也正因如此,两者又往往同时出现,几乎所有社会热点下,高赞发言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后来的评论中,类似的意思不断出现,极端情况下则是复制粘贴,形成固定的套话,而“标签化”也往往在这时入场。我们有谈到“标签化”带来的简单化结果,其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泛化、扩大化、极端化,从而造成“误伤”,类比到文学史现象中则是五六十年代对陈翔鹤等书写历史小说者的戕害。从结果来看,它已经令当代舆论场中的各方难以互相理解,形成更具攻击性的群体,在特定的社会议题中,则是身份群体的互相对立。
说来,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便是人类脱离群体社会,进入个体生活时代,结果也已经是彼此之间的隔膜,理解与沟通交流早已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这在以往的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而当代舆论场在误解和对立之中走得越来越远,实际上相当于为登山之阶增添路障,最终只会更进一步拉长人与人的距离。表面上,这一切只是发生在互联网中,但其实已经反映到了社会之中,就我所看到的,已经有不少人表示放弃交流。从另一个角度看,互联网的诞生本是便捷了个体的发声,然而如今主动放弃发声、消极应对的显现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也显现出一种背反。
再怎么说来,这个议题只是令我觉得当代生活不值得延续的一个方面,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的方法,甚至并没有被提上需要解决的日程。还原到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难以理解、不愿理解也要因为人际关系装作愿意理解以及不愿理解而造成的冷漠与百无聊赖都构成我对这个时代的反感因素之一。
敬老师说他绝对不愿意回到八十年代,因为那个时代的贫乏和这个时代丰富具有天壤之别。当时我觉得这种观点十分正确。现在想来,他们所带有的那种朝气、对未来的期待和动力,就像李厚晨说的:“可期的希望感,以及这种希望感所带来的追求和温和的氛围,是那个逝去的好日子最鲜明的特征。”而这些,在如今时代却早已消逝殆尽,用社会事件构成当代人一生的图谱之后,很难相信什么人还能继续保有这种纯情与天真。在此,存在主义的教条也显得那么无力。这就是为什么面对老师、家长甚至一些同龄人的不理解和一些发言时我只能苦笑的原因。
我羡慕不知这些的同龄人,羡慕那些能够有美好前程日日交流在哪个城市能够得到好的发展的同龄人,但我难以想象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或许我永远都位处“下僚”,或许我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说到底,是否努力的结果可能并不会差很多。读了好几本《十九首》专著,我还是只记得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曾经我也觉得自己不平凡,即便现在我还是会说:“不过凡人总会心有不甘。”但其实这些或许都很可笑,毕竟我只如雕虫微小,就算如愿又能怎样?
我想应该还会有一两篇文章与此篇构成同一系列,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笔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