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建构与瓦解——论沈从文的《夜》
【摘要】 《夜》是沈从文30年代“反复书写”创作倾向下完成的一组以军旅经历为主题的“同质异构”小说中的头一篇文章。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和一个叙事“圈套”营造出极强的代入感,并在后来的叙事过程中不断渲染整体氛围,使读者与小说人物心理体验逐渐“同化”,同时“设下悬念——打破悬念”的“轮回”叙事与多个地方传奇搭配,建构起小说的传奇色彩。随着悬念被一次次打破,作者建构起的传奇也就一次次被瓦解,直到最终的老人隐秘的揭示,“我”陡然陷入了巨大的惊讶和后怕。在这种建构与瓦解的过程中,沈从文完成了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表达。
【关键词】 军旅写作 传奇 生命意识
1927年底,入京近五年的沈从文暂时告别了他的窄而霉小斋,带着“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踏上了南行的旅程。这一次,“漂泊者”定下的目的地是上海。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一行就是三年的时间。在这短暂的三年内,沈从文逐渐摆脱了初入文坛时的青涩,结交到了一批文化界名人,并凭着这些“大佬”的荐举和赏识逐渐确立起自己在文坛的位置,他甚至办刊物、教书、写批评文章,可以说完全成为了新文学的“圈内人”。但这一切并没能改善他一直以来生活上的困难境况,为避难而从家远道而来的母亲和妹妹又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欠债、借钱、预支薪水和稿费始终与他如影随形,生活的苦闷达到了顶点。可似乎老天嫌他自己生活中的麻烦还不过多,在让他设法解决生存难题的时候又给他制造出一份棘手的“情感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下,沈从文“被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产作家”,而正是在这一批迫于生计而赶出的作品中,他逐步确立起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定位,并将20年代长期的文学实践转化为充足的养分,有意无意地迈入了作家创作生涯中必将见到的那扇名为“成熟”的大门。
考查这诸多匆匆集结起来的文章,不难发现,“军旅”一词成为论述这一时期沈从文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核心关键词,《丈夫》《柏子》之类的湘西风俗书写与他的军旅生活脱不开关系,《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我的教育》之类的文本则直接是“自传性”叙述。而在这一批作品之中,沈从文表现出了一种“反复书写”的创作倾向,除了笔者已经探讨过的《医生》和《三个男子与一个女人》之外,《夜》《山道中》还有《黔小景》构成了另一组“同质异构”式的书写,而正是在对这一组关于荒凉山道的先后书写中,显示出了沈从文一步步瓦解“传奇”的叙事倾向,更呈现出他对个人身份定位的某种模糊性。由于时间和篇幅因素,本文仅对最为独特的《夜》进行探讨,笔者试图通过本文还原沈从文对“传奇”的建构与瓦解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背后的指向做出个人解读。
一、悬念的“轮回”——《夜》之“传奇”
《夜》与《我的教育》《会明》《冬的空间》等篇目一起被收录在于1930年6月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沈从文甲集》中,它延续了这一时期沈从文钟爱的“叙事套盒”创作方式,小说围绕“我”与四个同伴兵士的山路夜行经历敷衍出一篇奇特“传奇”。
第一人称“自传性”叙述无疑在文本的开端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开篇的回忆性追述也在一开始就给人一种亲切和随意的感觉,然而在这种表面的漫不经心背后实际上带有叙事者很强的建构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与自传性叙述同时出现的真实事件——即《我的教育》那篇确实是沈从文所写的文章,还有榆树湾、槐化这两个沈从文确实曾呆过的地点上。正是这样一个有意为之的设置使读者很容易便落入了作者设下的“圈套”,进而成功引发了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我”与真实作者沈从文之间的混淆。问题则在于,这份叙述真的真实吗?答案是否定的。
1918年8月26日,杨再春率领的土著军队到达辰州准备接受改组,年仅16岁的沈从文正在这支部队里。后来,沈从文被编入“湘西联合政府”所属的“靖国联军”第二军第一游击队,这支队伍改归张学济管辖。到了9月,沈从文随所在部队被分派到芷江(沅州)榆树湾去“清乡”,四个月后,才又移驻到了怀化镇。[1]通过对比文本和沈从文的实际经历不难看出,小说中“我”先后到达的地点在悄然之中被调换了,这样一个细小琐碎之处的差异正说明文本内容与沈从文个人经历之间存在着人为撕开的裂缝,因而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将“我”与沈从文个人的经历等同起来。可这种“不等同性”显然是沈从文所刻意掩饰的,正如吴晓东所言,“当沈从文在故事中宣称自己所讲是真实的事情的时候,他所强调的并不是小说的真实性,而恰恰是借以征服都市读者的虚构性和传奇性。”[2]作者在小说一开篇便刻意地竖立起一种“自传性”,这无疑带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它所带来的结果正是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和阅读兴味,而这种由作者刻意建立起的引人注目也由此开始,贯穿了整篇小说。
《夜》并不直接写“我”的夜行,反而在开篇从“我”在清乡驻防时的所见所闻写起,在这一部分文字里既包含了对“我”被提拔为司书经历的讲述,又提到了《我的教育》里已经大书特书的“看杀人”,还说明了榆市与槐化是怎样的不同。这里所写的“我”对看割心肝一事的热衷和年幼时听到的“妇人炒舌头”的事件可以看作是对“看杀人”系列事件的补充。而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纹理,叙事者通过这一系列文字正是为了揭示出看似已经“成长”了的“我”身上的“变”与“常”(与《我的教育》里的“我”相对比),并且通过这“变化”来作为引出真正事件的引子,这也正是吴晓东所谓的“在正式进入故事的讲述之前,先指涉一下都市语境,其实正是对都市中的读者发言。”[3]而到了真正的事件叙述时,叙事者的“野心”才真正得到展露。
主体部分的开端是这样的:在一个“阴郁沉闷的南方二月天气”,刚刚升为司书的“我”被营长派去“距镇上约有二十五山里远近的一个冷僻岩上”抄写表册,随即“我”同四个从那里来领取筹饷的兵士一同在“烧夜火”的时候上路。在进入主体事件叙事后,叙事者先是经由“我”的双眼为读者描绘出山路的整体环境,一方面它险恶可怖,“有时爬上了岭脊,两面皆下陷无底,忽然又蜿蜒下降,入一个夹谷,在前面十丈仿佛即已到了尽头。随处是高耸的石壁同大而幽僻的树林。”另一方面,道路两边又显得极为荒凉破败,“从一些废油坊同废院落外面绕过时,望到这些工程伟大的长围墙,使人想起数年前这主人的光荣,总不能不把火把向那黑暗的冷落的空地照照。”在这里,叙事者在极力描述路途上“皆是这样不可形容的怕人的出奇的情景”的同时,指出了自己的真正意图,即强调几个年青人的大胆和无所畏惧,“一切皆是这样不可形容的怕人的出奇的情景,但在这些情景下,几个在军营中滚着日子的年青人,心粗气壮,平时大量的吃酒吃肉,这时沉默的或大声歌唱的走路,从这些人行为上使我心上的畏惧毫无长成机会,我就反而为那动人的美所醉了。”我所陶醉的“美”来自于这些青年身上天然淳朴、略显粗糙的不加雕刻的原始人性,它长久地保留在“我”的心中“到如今还不完全消失”,而这样一种根植在湘西人身上的淳朴天性仅仅由“我”所感知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我”的敏感和善于观察,在后文中,正是“我”身上的这种特性成为不断引发小说悬念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头看整篇文章的起始,从那些对驻防稀疏平常的文字中,作为读者的我们并不能料想到所谓“夜”是指夜行,而将视点放置在夜行途中,我们同样也不可能预料到叙事的走向最终落到了老翁那里。在这样两次叙事方向的转变过程中,整个故事从散文化的日常转向了带有刻意性的“传奇”,在从夜行转向孤老的过程中,起到衔接作用的正是一次又一次悬念的设置与破除。
(一)声与光构成的悬念
第一个悬念是由声音构成的。到溪边的时候由于无法渡河,一行人陷入了去向的纠结,什长是有经验的人,但他所提出的向下游走去的意见却因为“一种仿佛距离很近至多不过在半里以内的奇怪声音”而被否定。叙事者通过“我”为这声音做出了预设:“只有水碾子同油坊两种地方才会有的”,而水碾子和油坊正可以提供他们所急需的落脚地。向上游走去的过程中,声音被赋予了一种“召唤”意味,“我们好像觉得越走越与我们所听到的那种声音距离较近”。在“已经走了两个钟头或三个钟头不遇到一个活人以及一间有灯光的房子”后,一行人因为“夜行的空洞寥阔心情,太需要一点温暖以及一个休息的地方”,而迫切希望能够尽快到达声音的发出地,在这样一种由“我”——一个第一人称所建构起的近乎主观的叙述氛围中,读者的阅读期待也被顺势勾起,因而读者开始与“我”们一行共同分享心理体验——迫切希望到达声音的发出地。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叙事者设置了一波三折的“险情”:一方面是火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道路的坎坷难以防备,这加剧了读者的惊恐体验。在这里,“夜”成为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叙事空间,作者通过此前对山路状貌的描绘在读者心中营构出了一个恐怖的整体印象,它的荒凉颓圮还有坎坷崎岖正带有一种侵蚀生命的意味,而寻觅声音发出地过程中的火把将要耗尽带来的正是“陷入黑夜”的恐慌感,在山道中陷入黑夜的结果则是灾难甚至死亡,叙事者正是通过对这种恐慌感的营造,悄然提升了“我”们对声音发出地的期待值;而“声音”则成为了通向生的钥匙,成为人物勇敢向前的根本动力,成为“化险为夷”的唯一可能。
然而,当作者将声音带来的悬念感塑造到顶点的时候却突然亲手拆解掉了它:随着声音的临近,“我”们明白了这声音是一个水车的声音,而“声音所在的地方毫无灯光……这打击使我们五个人皆骂了一句娘。我们是被这东西所骗了。”水车旁没有可以落脚之地的现实带来的一种期待落空感同时出现在读者和故事中的人物身上,一方面“我们五个人皆骂了一句娘”,这实际将读者的感受一起抒发了出来,另一方面又透过对声音态度的前后对比显示出这种落空感对“我”们的影响(此前是好奇期待,这里则认为发出的声音是“大而可恶”的,“似乎把我们骗了还在那水中嘲笑我们这一群年青人是呆子”),从而将读者与人物分离。
不多久,当“我”们爬上山顶试图寻找落脚地的时候,第二处悬念出现了。“到了山顶以后各处一望,望了许久,山后的灌木林后面远处,被我看出一点火光了。我们大家注意到这相去一里以外的小小火光。”火光带给五个青年们的期待感再一次被拉满,“前面一点小小光明使我们忘了一切危险,我们随从什长越过了许多阻碍,越过了许多有水的湿地,又从一些灌木林里奔过去”。这里的心态既符合“我”所提出的那种勇敢直前的年青人性情又给读者以一种“怎么不长教训”的感受,而随着距离的拉近,读者先前的预感得到了作者的“回应”:“这时什长忽然机警起来,恐怕前面等候我们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危险,变更了我们前进的计划”,突如其来的小心翼翼和紧张兮兮再度勾起读者的兴致,同时也再一次设下了新的悬念。为了让这种看似突兀的紧张显得自然而然,作者安排“我”发声解释了精神紧绷的原因,“我们在任何情形下本来皆缺少吓怕的情绪,经过了许多的危险,且常常像这样子在深夜包围一个匪巢,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了。但到了这时,各人的心仍然好像是绷紧了……我这样思想时并不是怎么害怕的,我的同伴当然也不怎么害怕,我们各人有一支单筒盖板枪,有一百六十粒子弹,在任何情形下都很有把握可以凭这点东西换他们二十条性命。不过时间与空间放到那地方那种情形下面,使我们各人皆有理由为这寂静的沉闷攻袭,心上感到冰冷,几几乎要放声长嗥。”这份说辞的核心显然是在强调年青人是什么都不怕的,但它在最后却又推翻了前面的自我建构,通过不断渲染紧张的气氛揭示出“我”们一行人在那时的神经紧绷,正是这样一种先建立再打破的叙事方式设立起了读者对可能发生的交火冲突的不详预设,增强了整个情节的悬念感。而这还不算完,沈从文更刻意的建构随之出现,“我”因为敏感和善联想突然在此“时节忽然想起了施公案一类故事,以为在那里一定是一群强悍凶狠的人物,且想起我们营里不久日子才捉到那匪头被镇上人破腹取心的事,以为这屋里若是一群土匪开会决议报仇方法,我们什长这一去,不到一会就应当破腔取心作醒酒汤了。”通过对这样一个近乎传奇事件的补述,刚刚已经被拉高的读者的阅读期待再次得到了强化,而这种近乎传奇的事件也拉开了此后叙事中“传奇迭出”现象的序幕。
在整个情节的最后,作者通过调换视角来继续强化悬念感,“我们看到什长走近那人家了。我们看到什长在拍门了。我们听到什长在同人说话以及一只小狗的吠声了。”这样一种类似电影聚焦镜头的目光让读者通过“我”们之眼凝视着什长身上发生的一切,重复的排比书写则强化了这种聚精会神的凝视带来的精神紧绷感,而当“拍门”之后随即出现的是平淡的“同人说话以及一只小狗的吠声”时,此前曾建构起的期待和悬念也就“轰然倒塌”,“因为听到拍门,就明白是可以不必开枪的生意,到后又听到小狗的吠声,更明白是平安无事了。一个匪巢是不会把大门严闭一直让人到他的门外拍打的,一个匪窝更不会喂养一只小小的无用处的狗,这就是我们对于从经验得来的知识。”在这份叙述中“我”的失望再度显现出来:没有危险本应是好事,但通过刚刚设下的一系列悬念,结局的平淡反而成为溢出期待的内容,由此才令“我”们深感失望;而在读者这里,其结果则还可能是松了一口气。两种面对期待落空的不同态度正显示出“我”们与读者之间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源于“我”所一直强调的年青人身上勇武的特质。
在第二次由火光生发出的悬念中,作者通过各种笔法建构起读者高度的阅读期待,这种刻意举动大大强化了读者对故事的代入感,从而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暇思考这种叙事究竟是否是真实的,也正是通过第二份悬念,作者完成了对叙事重心的调整,在此时,小说的面目已经远离了开篇时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式的闲散,而逐渐显露出它潜伏的传奇性来。
(二)林间老翁与悬念的建构、瓦解
老年憔悴的男子的出现提供了完成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块拼图。几乎从他的一出现,悬念感和传奇色彩就集中依附在了他的身上。“为什么会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住下”自然而然地成为读者所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继而他身上的忧愁和憔悴又成为第二个关注点。两个问题的答案均被有意悬置——什长并不过问老人的情况,直到文章末尾才由他自己之口揭示出来,而这样悬置的结果则是“我”开始擅自为读者提供问题的答案,作者也借此使老人的寡言与“我”的思维活跃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个情节单元中,作者通过“我”之口一直在刻意地塑造着一种传奇性:进门时“仍然不忘记人肉包子迷魂汤一类故事上的危险事情”在平安入屋后被打破,入屋后发现“老人家中的简单同干净,忽然又使我疑心我们今晚上所遇到的是神仙了”,而这种对他脸上“非凡的光彩”的期待又在看到《庄子》时被击碎,但“我”仍旧不愿放手,“总仍然以为这个人是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物”,“猜他不是个神仙也一定是一个隐者”并继续将“英雄的梦转到神仙的梦”上。在“我”的身上,一种非要平地生奇的愿望过于明显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土匪到神仙再到稀奇古怪的隐者,预设的一次次被颠覆带来的是悬念在表面上的一次次设立与瓦解,而每一个被瓦解的悬念都又更进一步抬高了读者对老人身份的期待感,作者通过“我”的视线刻意赋予老人一种传奇性并唯恐读者没有发现老人身上的“不正常”而不断进行刻意地提醒,无论是脸色的忧愁和不高兴,卧房床铺上睡觉的人影,不便为人做饭但却不断帮忙,还是最后把卧房“扣了一把铜锁”以及那句耐人寻味的“好像不是我陪你们,是你们陪我”都使这个接待“我”们的老翁显得不那么平凡,他像是在有意掩盖着一些事情,因而令人不禁持续地将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这种通过“我”的刻意关注而引起读者注意的方式表现出作者鲜明的引导意识,这种引导从一开始就指向了传奇并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不断深化这种指向,这就引发了围炉夜话的桥段。
在“围炉夜话”中,作者终于不再隐讳地从猜测中建构传奇性,而是一连串写出了好几个湘西传奇。老人虽然参与了这个传奇故事的讲述环节,但自始至终却并未言说任何内容,他的神秘性一直保留着,并通过“我”天真的猜测而做出解释。实际上,笔者认为被视为传奇的老人参与到以传奇故事为主题的夜谈里本身就是对传奇性的一种瓦解,这说明他并非什么仙人高士,而是也十分关注最简朴的民众言谈的普通人,但这份潜在的暴露由于“我”在兴头上和那些传奇故事对读者的强大吸引力而被完好地遮掩住了。当围炉夜话接近尾声,老人终于告诉了“我”他所掩藏的秘密。在随他前往卧房的时候“我”还没有放弃此前的想法——近于顽固地认为“他一定是有许多宝物在房中,并且一定还得传授我什么秘法同到兵书”,这样的叙事将原本逐渐冷淡下去的读者期待再度拉高,悬念也就再度得到了强化。然而当房门打开,我却失望至极,因为“房中除了一些大小干果坛罐,就只是一铺大床。这里床上分分明明的是躺着一个死妇人。一个黄得黄脸像蜡,又瘦又小,干瘪如一个烤白薯在风中吹过一个月的样子的死人。”至此,在小说的末尾,作者通过揭示老者的隐秘将一直以来的不断建构的悬念的“轮回”终结,同时也将此前辛苦构建的传奇性一并瓦解。
通过对整体文本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极强的刻意建构意识,他通过第一人称和一个叙事“圈套”营造出极强的代入感,并在后来的文本叙事过程中不断渲染整体氛围,从而完成将读者与小说人物心理体验“同化”的过程。随即他又开启了“设下悬念——打破悬念”的“轮回”叙事,并为这种“轮回”叙事配上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从而建构起小说的传奇色彩,而随着悬念被一次次打破,他所建构起的传奇也就一次次被瓦解,直到最终的老人隐秘的揭示,“我”陡然陷入了巨大的惊讶和后怕。笔者认为,正是在这种建构与瓦解的过程中,沈从文完成了对自身生命意识的表达。
二、军旅创作与生命意识的养成
在第一节的开头部分笔者已经对沈从文早年的军旅生涯状况稍作了说明,而纵观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不难发现,军旅生活的影响对于他个人而言是十分强烈的:一方面,他随着开差的军队游历了湘西各地,这对他了解整个湘西地域的风土人情有着十分重要的帮助;另一方面,军旅生涯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影响了他人生观念乃至生命意识的形成。正因如此,对军旅生涯的回忆一直是他湘西文学创作的“重头戏”,这几乎贯穿了他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初的整个文学创作历程,有论者统计,仅在1925年—1930年这六年中,他便创作了21篇描写军旅生活的小说[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大都采取了同《夜》相类似的“自传性”写作方式,而这些书写也正如朱寒汛所言:“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士兵生涯的追忆和眷念:军人在他的笔下不是杀人的魔鬼而是自己生命的镜子。他们或嗔或喜,在青山绿水之间飘荡,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与悲哀,梦想和尊严。”[5]可以说,通过对“军旅人生小说”的大量创作,沈从文逐渐确立起自己对于生命意识的初步理解。
具体到《夜》中,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观念一方面体现为对美好人性的热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死亡问题的思考。前者在第一节的文本分析中已有涉及,总的来看,“我”对同行的青年军人的“美”的评价正是基于他们身上那种淳朴粗糙不加雕饰的原始人性,他们的勇敢和无所畏惧是为我所喜爱的,这正是他所意欲在自己的“希腊小庙”中供奉的美好人性所具有的品质,然而他并未就此将这些青年兵士简单化和概念化,在面对死亡问题时,他也直接揭露出他们身上复杂的一面。
在《我的教育》中沈从文详细揭露了湘西军人面对杀人和暴力时的愚昧和可怖心境,在这里,杀人成为唤醒生活、寻求刺激和享乐的方式,“除了杀头,没有算是可以使这些很强的一群人兴奋的事了。”因而,杀人也就成为每天定期上演的“戏码”,小说中“我计算下一场必定仍然至少还有四个,因为五天内送四个匪来是可能的,并且现在牢里就还留得有四个,听他们说是有两个本应昨天杀掉,因为恐怕下场无人杀,所以预备留到下场用的。”正揭示出杀人成为每日固定“节目”的现实,被杀者在前几天就已经备好,目的就是为了每日例行完成“任务”。在这种书写中,沈从文揭露出兵士们顺遂天性(即最基本的享乐欲望)的一面,他用“天真”一词来形容参加赌博的成年兵士们:“虽然许多人已全是做父亲的年纪了,对于玩,还是很需要的事,他们心上全是很天真!”然而我们很难说他在诉诸笔端时所想要表露出的仅仅是对所谓“美好人性”的赞美,相反,在这种“美好人性”背后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警示意味——他揭露出湘西人的愚昧和落后,“天真”在此处正是对这种愚昧无知的反讽。相较而言,《夜》对于兵士对死亡的麻木和愚昧状态仅仅是点到为止式的书写,但即便如此也仍体现出沈从文对于“死亡看客”的批判意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是“我”。换防后的“我”成为司书,但这样一个与“文化”有关的职位并没能改变“我”爱看杀人的喜好,“除非正在写一件顶要紧的公文,我总得抽空去看看,看到底有人割心肝没有。”这样一种心态正反映出年少者的无知和愚昧。
如果说《夜》开头的看杀人叙事与此前的文本可归为同一序列的话,那么让这篇文章区别于其它文本地方正在于小说末尾的死亡设置。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对待死亡态度的两次转变:最先是从高度期待到期待落空的失望感,继而是听了老人的话后生出的惊讶。从前者看,“我”对死人的失望完全是基于个人意愿生发出的感受:在这里,死人本身带来的冲击几乎为零,整体情绪的转变完全出于个人期待的落空,这种对死人的漠视态度巧妙地同整部小说的开篇处那些若无其事的“看杀人”文字达成了对应。从后一次转变看,我的惊讶与后怕来自对老人面对亲人死亡时所表现出的冷静态度,他本想伴着亡妻睡一夜,但“我”们的到来打断了他,而他则静静地听我们讲了一夜的故事,面对老人的冷静“我”受到了某种触动。在笔者看来,这种触动实际是面对死亡的两种不同态度带来的。
“我”由于长期看杀人而养成了对死亡的麻木态度,这是因为死者均与自己无甚关系,在这种前提下,看杀人成为军队中的“我”“享乐”和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而老人对于亲属死亡的冷静则显示出湘西人“对死亡的默认和对悲痛巨大的忍耐力”,《庄子》的意象正是对老者态度的一种预示,而这种在死亡面前显露出的“自然数尽,从不悲泣”的超脱态度背后存在着一股悲哀的潜流[6],作者在小说的结尾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当我把水烧热,嗾醒那几个倒在火堆边睡觉的同伴兵士洗脸时,我听到一个锄头在屋左边空地掘土的声音,无力的,迟钝的,一下两下的用铁锹咬着湿的地面。”这种无力迟钝的掘土声所唤醒的正是一种源于楚人的血液所带来的“命定的悲剧性”(《长庚》)[7],老翁独自掘土的背后实际上揭示出的是真实生命在面对死亡时所回归到的本初的孤独状态——他和沈从文笔下那个死在船上的老兵一样(《烛虚》)[8],令“我们感受到的是生命最本初的寂寞,最单纯的悲伤,这是不掺杂任何复杂成分的情感。”[9]这是造成“我”惊讶的来源。这种面对死亡的感受与“看杀人”时的麻木和空虚有着巨大差异,前者所展现的是生命走向终结的原初过程——这是一种由纯粹的偶然性建构起来的生命历程,而后者则是完全人为造成的悲剧,在近乎麻木的冷漠叙事背后显示出的是沈从文对这种滥杀行为的讽刺和批判,这正如刘洪涛所言:沈从文在叙述“湘西世界充斥的暴力、劫掠、血腥”时所呈示的“蒙昧的叙事态度”,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伪装”成分。如果剥离了这层“技术伪装”的面具,就不难发现沉潜于文本深处,对国民弱点的剖析与谴责,以实现人之现代化的意愿。[10]
由此,小说末尾处的死亡叙事所显露出的是沈从文此前未曾表露出的一种生命意识,它与看杀人叙事中对权力滥用与愚昧国民性的批判不同,在这里表露出的是一种原始的生命意志,死亡本身“命定的”偶然性和对人生的终结意义被一种淡然的观念所含纳,从而成为文本“朴素的悲哀”的来源,这种生命意识是顺遂自然的,而为了还原这种朴素,沈从文才不惜费心费力地一次又一次建构起传奇性并最终将它瓦解,因而可以说,传奇的最终瓦解和“我”对于死亡态度的最终转变在文本末尾老人的掘土声中最终走向了统一。
引文:
[1]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9-10.
[2]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2):84.
[3]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2):85.
[4] 袁启君.论沈从文军旅小说的内涵[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4):42.
[5] 朱寒汛.青年沈从文军旅小说略论[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刊),2008,2:59.
[6] 刘自然.论沈从文小说的死亡书写[D].南京:南京大学,2011:12.
[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散文[M].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39.
[8]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散文[M].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15.
[9] 刘自然.论沈从文小说的死亡书写[D].南京:南京大学,2011:29.
[10]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5. 转引自 洪耀辉.论沈从文小说中“杀人”叙事的精神向度[J].江西社会科学,2009,3:129.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五卷):小说[M].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2002:152-173.
【2】吴世勇.沈从文年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刘自然.论沈从文小说的死亡书写[D].南京:南京大学,2011.
【4】张迪.沈从文小说的死亡叙事[D].长春:吉林大学,2017.
【5】刘西越.沈从文创作中的情绪记忆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8.
【6】韩立群.童心映照的军人世界——论沈从文的军旅人生小说[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6:60-70.
【7】熊峰.沈从文短片名作《夜》的隐喻内涵与叙事构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7(1):56-57.
【8】朱寒汛.青年沈从文军旅小说略论[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季刊),2008,2:55-61.
【9】袁启君.论沈从文军旅小说的内涵[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4):42-46.
【10】洪耀辉.论沈从文小说中“杀人”叙事的精神向度[J].江西社会科学,2009,3:128-131.
【11】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2):82-89.
【12】刘晓静.人生悲凉和历史图景惨烈的双重书写——对沈从文小说《黔小景》的解读[J].名作欣赏,2011,30:28-30.
【13】汪纪明.叙述中的“时间”——以1930年代三部短篇小说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9(1):109-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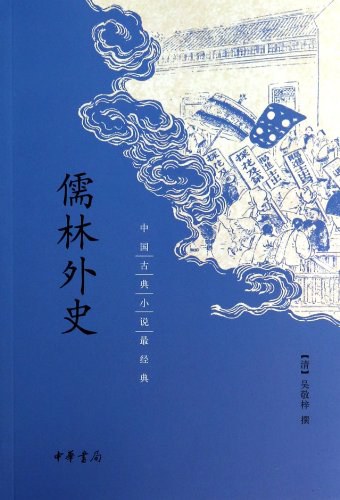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