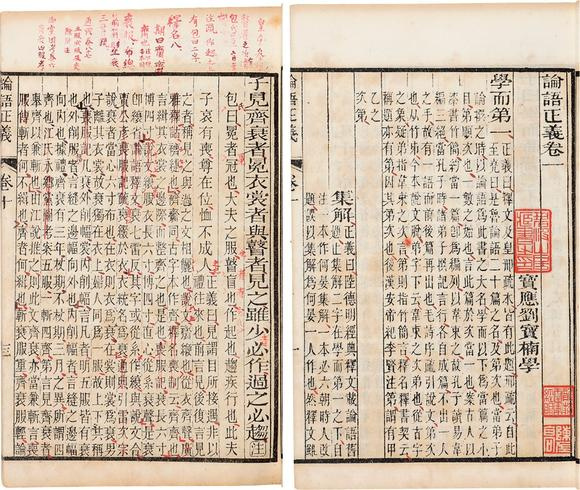浅析罗马共和国末期及帝国前期的道德状况
【摘要】 古罗马的社会道德状况在共和国末期及帝国前期这段时间内从原本的淳朴务实、善良勇毅渐趋堕落腐化,这是由财富激增、劳动力过饱和、军事政治制度变革等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希腊化时期所产生的伊壁鸠鲁主义以及斯多葛主义在为这一时期迷茫无措的罗马人提供心灵慰藉与行为凭依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道德的下滑,并且为罗马最终走向灭亡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 古罗马 社会道德 伊壁鸠鲁主义 斯多葛主义
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前期这四百多年间,古罗马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它经由数次对外扩张战役,从一个走向衰亡的共和国转变为一个将地中海囊括于腹中的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然而在疆域不断扩大、财富持续累积的繁盛表象背后,这艘曾经乘风破浪于波涛汹涌的历史之海中的巨舰实际上已经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驶入了无法逃离的漩涡——这种情况在这一时期社会道德的腐化堕落中集中体现出来。本文试图在简述古罗马这一时期社会道德由淳朴向堕落转变的现象的基础上探讨斯多葛主义以及伊壁鸠鲁主义同这一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道德的腐化与堕落
如果说古希腊的先人是通过崇高华美的艺术以及渺远深邃的哲理思索为后世留下无限的精神遗产的话,那么作为承续其后的古罗马人则是通过一种气势雄浑的英雄主义品格以及环绕其左右的高尚品质激励着后世西方人的情怀。
不似通过漂泊于各个港口之间进行商业贸易而起家的希腊人,罗马人民将农业为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农业民族的特性铸就了罗马民族所独有的崇尚勤劳与节俭的社会风尚,而这也被视作一种优良的民族传统为各代君民所遵从:临危受命并在解救国家于水火之后拂袖而归的辛辛纳图斯[1]以及共和国时期曾四次担任执政官、“荣誉巨大,但家庭财产却如此微薄,甚至都不够葬礼费用,结果由国库提供”[2]的普布利科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古朴的风气在促使罗马人遵循勤劳与节俭生活的同时也令他们获得了诚实正直、信守承诺的良好品质。在李维笔下,罗马人即便是在涉及生死存亡的战争时也不忘遵守这一行为准则:“我们的祖先决不用埋伏的方法打击敌人,决不在夜里向敌人发动袭击,也决不用假装逃跑然后突然转身的方法向那些还未作好准备的敌人发动进攻,更不以狡猾而以真正的勇敢为自豪。”[3]这种行为无论是放在当时还是现如今都显得极为可贵,虽然在战争中它也或多或少地有些迂腐愚笨,但也正因如此,罗马人才会得到世人发自内心的敬意。
作为古罗马文明精神的核心,整个社会中所漫溢着的功利主义以及英雄主义观念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种极为崇高的为了国家利益和荣誉不惜牺牲自我的爱国精神,这与罗马人频于征战扩张的现实是相一致的。在一次又一次发起的对外战争中,罗马不仅从一个起初只有七丘之山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大国,而且也为它的民众刻上了刚毅勇猛、凶残顽强的烙印。在这种普遍存在的道德品性的指引下,罗马人在原本的社会内部形成了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并且以其战无不胜的军队横扫了一切试图阻挡他们脚步的敌人。除此之外,在行军过程之中形成的严明的军纪也在某种程度上使遵纪守法这一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人心。
总体而言,生于农业文明的罗马民族有着非常朴素的求真务实的功利意识,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勤劳节俭还是为了生存或自卫而进行的扩张战争都出自于此,在这一层面上,早先罗马的社会道德确实具有淳朴贤良的特点。然而,当历史演进的路程行进至共和国末期与帝国早期之时,除了功利意识之外,上述的这些良好品质似乎一个个都在风烟之中消逝了。
当经年累月的征伐告一段落,来自天南海北的奴隶、战俘和金银财宝如同百川汇流一般源源不断地聚集到罗马原本的城市之中,战败者所支付的巨额赔款抵消了罗马人所需缴纳的税赋,曾经需要每日工作的人们现在可以坐享其成,守邦卫国的军人由义务服役的公民变为向钱看齐的佣兵,这些情况一方面使得个人主义观念迅速席卷人们的心灵:曾经那种能够替罗马事业赴汤蹈火的集体主义爱国观念业已成为一触即破的泡沫,人们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地收敛财产,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因此被快速拉大,如果说此前的罗马人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压抑私欲,那么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则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欲牺牲国家;另一方面罗马人民也因此获取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在这种情况的驱使下,市民们每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并逐渐沉溺于声色犬马、奢靡享乐之中,“世人把占取巨量财富视作荣誉的标志,昔日孜孜以求的忠诚、勇武、勤勉、奉公、节俭之类德行,却近于绝迹了。”[4]德米丰直言:“我攒够了钱,我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我还包养了情妇。我的妻儿对此并不知情……我来日无多,我要让欢乐和酒色陪我度过有生之年。”[5]萨卢斯特也在书中指出:“乡下的年轻人靠劳动难以维持生活,就在生活富裕的城里人帮助下来到罗马谋生,他们发现城里生活安逸,就不愿意返乡务农。”[6]
如果说个人的行为造成并反映了社会道德的崩塌,那么政府和国家的做法实际上在有意无意中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崩塌的过程。大量劳动力的涌入致使城市失业率急速提升:根据公元前22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这一时期的奴隶人数由公元前2世纪的60万猛增到了300万,增幅达5倍。[7]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保障失业人员的生存,政府为失业者提供了不限于饮食的充足援助,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举措非但没有减轻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反而更进一步加重了劳动者消极倦怠的心理。在后来的帝国时期,许多由国家出钱举办的公共娱乐活动诸如角斗、赛车和洗浴逐渐成为满足罗马公民生活以及精神需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这些活动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作为一种联系百姓的纽带而存在的,它们在宣传教化、安抚民众不满情绪的同时也维护了君王自身的统治。
由此,种种现实都真切地向我们展示出这一时期罗马的社会道德正在向着一个无尽的深渊缓缓地坠落,它受到一种来自群众的强力的牵引以至于在统治者试图以法律扭转这种日下的风气时也无力回天。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除了受到上述物质生活、社会现实的影响外,其背后实际上有着更为深层的思想原由,那即是希腊化时期所兴起的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
二、两种伦理思想与道德堕落的关系
与其它文明一样,转型之中的罗马经历着由巨变带来的阵痛与迷茫,新的社会现实让曾经巍然耸立的高尚观念在这次变动之中轰然倾覆,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新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要求——肉体上对欲念刺激的疯狂渴望以及精神上对精神解脱的热切追求,然而正是这两种要求将罗马人带入到一种更加深重的苦痛之中:在肉体上越是放纵无度使得他们精神上就越是空虚无聊,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反过来又刺激了肉体的进一步堕落。[9]当罗马人民站在旧道德的废墟上开始试图重新建立自己新的精神家园时,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这两种希腊末期的伦理思想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只不过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两种思想在救疗人们茫然无措的心灵之时也为整个民族的衰亡埋下了深远的祸因。
对于这两种思想同这一时期社会道德堕落现实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单向式的影响而是两者互相选择的一种结果,可以肯定的是,两种思想之所以为当时的罗马人所使用,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其中的某些观点来为自己的行为寻得某种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当思想同人的意识相衔接,由思想而来的各种影响也就会悄然而至。
作为伊壁鸠鲁主义的核心观点,快乐至上的思想很明显地被罗马人拿去为他们奢靡享乐的行为开脱。从伊壁鸠鲁学派本身的观点来看,它将快乐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是自然的快乐,它源自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强调的是一种被动获得的愉悦,例如由惊喜的生日礼物以及出人意料的好消息带来的欢乐;二是非自然的快乐,相较于第一种快乐而言它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主动性;第三种快乐则在第二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它是由贪心、纵欲而生的欢乐。在伊壁鸠鲁看来,人存有欲望是正常的,但这些欲望在行动上却应该被制止,因为从伦理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快乐就是善,并且人生的幸福“最好能通过遁世绝俗、在几位朋友陪伴下培育一种悄然存在的纯粹快乐来获得”,在这个意义上,由欲念所生的欢乐实际上正违背了“善”,它是一种“不义”之行。因此,孟德斯鸠所言实际上是不妥当的[10],与其说伊壁鸠鲁主义腐蚀了罗马的人心不如说是罗马人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凭依时蹩脚地曲解了伊壁鸠鲁本人的意见。在另一个方面,仍旧以“快乐”为出发点,伊壁鸠鲁对于人类的苦难也怀有一种强烈的悲悯之情以及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他宣称世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他们不能逃避死亡,但只要能按照他的箴言审慎地生活下去的话,人们或许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于痛苦。这一教谕实际上是一种温和的福音,但对当时的罗马人民而言,已经足够激发起他们的热情。[11]
在上述这种曲解的情况下,罗马人开始按照伊壁鸠鲁的思想行事,而这也使得他们在贪欲方面变得愈发的肆无忌惮:许多贫民、奴隶为了追求金钱财富落草为寇,他们不惜抢掠老人和妇女,甚至想出将活人缝入死尸这样的酷刑;流浪者们通过迷狂的阵仗骗取钱粮,并且为了性欲一同染指纯洁的少年;女人可以为了情欲而欺骗丈夫和儿子,有时不惜将其置于死地,更有甚者竟愿同野兽媾和。[12]在“快乐至上”的教条下,曾经盛行于世的高尚与理性被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所取代,作为物欲拥有者的人在这种迷狂之中反而成为了物欲所主宰的对象,由此,被部分曲解了的伊壁鸠鲁主义带给整个罗马社会的是道德的进一步堕落。
如果说伊壁鸠鲁主义为这一时期罗马社会之中的纵情声色,贪图安逸以及崇拜金钱等使人“欢乐”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的话那么斯多葛主义则为罗马人民及其统治者构建了新的思想图景,正如吉尔伯特·穆莱所言:“几乎所有的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我们可以说芝诺以后历代所有主要的国王——都宣称自己是斯多葛派。”[13]
斯多葛主义的伦理观念是由其宇宙决定论所衍生出来的,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最初仅存有火,在这一基础上其它诸如气、水、土等元素依次产生,但无论如何终将有一场宇宙大燃烧使得这一切的又归于火,需要注意的是,多数斯多葛派学者认为这场燃烧并不是最后的终结,而仅仅只是一度循环的结束,整个过程将是永无休止的轮回。由此出发,所谓的“宇宙决定”即可被看作整个宇宙直到最微小的细节都是被设计而成的,并且要以自然的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设计者是“神”或者“宙斯”[14],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即是火,总的来说,“神”就是世界的灵魂,由火组构而成的事物共同形成一个叫做“自然”的体系;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份子,当个体的生命与“自然”相和谐的时候,它就能够达到某种超凡的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和谐则可以通过“德行”这种品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多葛学派的这种宿命论或是宇宙决定论一方面将万物的变化和不可知的命运理解为一种有规律的心智和理性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提出万物归一、不断轮回的观念,这就使这种观点在染上宗教色彩的同时又有着某种消解神秘的性质,但也正因如此,彼时茫然无措的罗马民众才会择取这样一种具有某些救赎意味的观念来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除此之外,通过对宇宙决定论的推演,我们可以进入到斯多葛学派的伦理观念中。德行作为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伦理概念,这些哲学家不仅认为它“是人生命中唯一的善”,而且也将它看作人自由意志的代表:“每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解脱出来,就有完全的自由。”[15]这种对于人生自由的宣告在爱比克泰德那里上升到了极致,“你可以把我的腿锁起来——不错;可是我的意志——那是你锁不了的,连宙斯都征服不了它。”[16]与此同时,因为所有的人都分享神圣的“火”,所以人人都是这样一个世界性社区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并且,他们也都被要求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即以德行事),从而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述的这种超越时代与地域的世界意识同样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得到了鲜明的展现:他不仅认为世人都是“宇宙公民”而且认为奴隶和别人一样都是“神”的儿子。这种由德行伦理思想与宇宙决定论生发出的自由与平等观念在实际上也确实为这一时期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罗马帝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陆续得到公民权的外邦人以及相对独立宽松的统治模式都是其力证。
然而即便如此,这一时期的斯多葛主义在普罗大众那里还是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人们虽然认同这些学者(他们又常常是统治者)所提出的道德标准,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仍旧遵照伊壁鸠鲁的“快乐至上”原则沉溺于奢侈、享乐、纵欲与无所事事当中,更有甚者,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本身也难以做到他们所提倡的德行一致[17]。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种无力还是出于当时那种和平、繁荣没有忧患的生活环境以及由此而生的纵欲、怠惰的社会氛围,而当这种腐化在偌大的帝国境内疯狂地蔓延开来,以至于人们逐渐意识到“已往之不谏”时,这个国家已经由于陷得太深而再也不可能从这深深的泥潭之中拔足而出了。
时间推进到帝国的后期,罗马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一切道德传统都已经荡然无存,伴随着社会道德的垮塌,整个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也终将走向瓦解,曾经维吉尔诗中所赞誉的伟大的七丘之城的子民再也无法缔造出往日的辉煌,等待着这个跨越了千百年风霜的国度的就唯有在苟延残喘之中慢慢地了结此生……
参考文献:
【1】《罗马盛衰原因论》,(法)孟德斯鸠著,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西方哲学史》(上),(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金驴记》,(古罗马)阿布列乌斯著,刘黎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古罗马人的欢娱》,(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王长明、田禾、李变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西方文化概论》,赵林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西方思想史》,(美)塔纳斯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
【7】沈坚,《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散论》,《史林》,1992年第3期。
【8】胡铂洋,《论帝国前期古罗马公民的社会道德》,2009年。
【9】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光明日报》,2012年9月3日第13版。
[1] (古罗马)李维著,王焕生译,《自建城以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II,26-29。
[2] (古罗马)李维著,王焕生译,《自建城以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II,16,7。
[3] (古罗马)李维著,王敦书选译,《建城以来史》,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XXXXII,47。转引自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光明日报》,2012年9月3日第13版。
[4] 沈坚,《罗马帝国衰亡原因散论》,《史林》,1992年第3期。
[5] 见于普劳图斯《商人》,引自(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王长明、田禾、李变香译,《古罗马人的欢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6] 见于萨卢斯特《喀提林的阴谋》,引自(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王长明、田禾、李变香译,《古罗马人的欢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7] (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王长明、田禾、李变香译,《古罗马人的欢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8] 一般是上午举行赛车与斗兽,中午行刑处决死囚,下午才是角斗表演,然后是去洗浴中心休闲。见于杨俊明,《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罗马帝国的兴亡》,《光明日报》,2012年9月3日第13版。
[9] 赵林 著,《西方文化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5页。
[10] “原文是:我以为在共和国末期传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大大地有助于腐蚀罗马人的心灵和精神。见(法)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2页。
[11]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3页。
[12] 以上内容均见于(古罗马)阿布列乌斯著,刘黎亭译,《金驴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3]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0页。
[14] 例如芝诺认为“神”是有形体的实质,是世界的烈火心灵,它与心灵、命运、宙斯都是同一个东西。见于(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2、325页。
[15]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2、323页。
[16]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3页。
[17] 据说塞涅卡聚积了大量的财富,价值达三亿赛斯特斯之多,并且大部分是由于在不列颠放贷而获得的。见于(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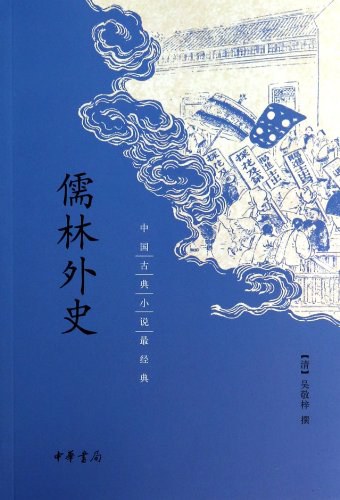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