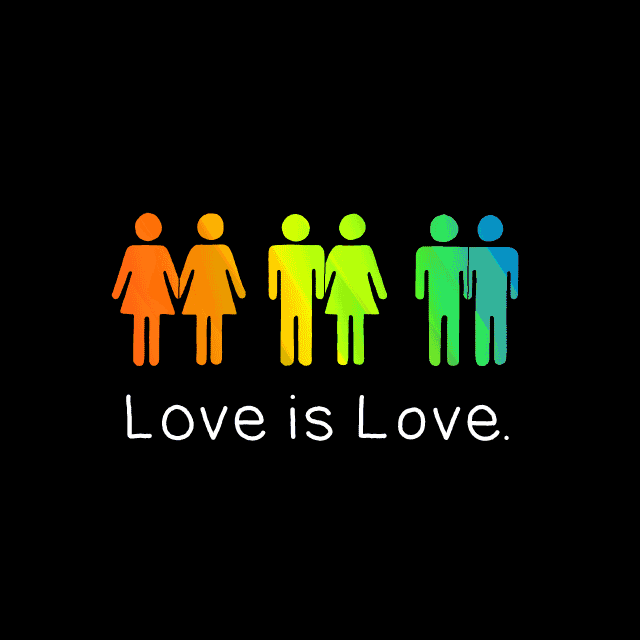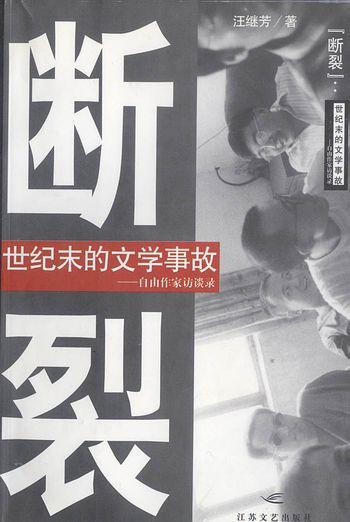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狗日的粮食》读后:匮乏、新写实、文学史的写作及其他
当代文学史把刘恒同方方、池莉、刘震云放在一起称他们为新写实。我想这着实又是文学史带来的一个误导,但也多亏了这误导,阅读的体验少有的令人舒适。毕竟阅读经历中符合期待、低于期待往往是常态,超出期待的情况总是难以遇到的。仔细想来这不过是当代文学步进九十年代后老生常谈的批评与创作乃至生产之间脱节现象的又一个表征——当批评家试图通过一些看似严谨的能指框定一些看似相近的文学现象时终会出现这样类似的尴尬(这并不是说命名是无效和无价值的,看似光滑表面中存在的那些缝隙才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这就要求我们看到这命名在哪里显示出无效,又为何如此)。
在我看来,刘恒的重要性在于他成为当代文学从八十年代后期对历史、文化、非现实和技巧观照向九十年代初期重回现实重新书写现实这样一个过渡时代的缩影:在《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与余华、残雪等一众先锋作家一样的冷酷、残忍、淡漠,看到与《爸爸爸》《九月寓言》近似的对于传统的反思和揭露;也能在《虚证》《白涡》那里看到时间步入至现代社会时的人心灵的卑琐、被戕害;即便是在题材上,从寻根的历史叙述到悬浮的城市风景,也正是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文学最大的不同,后者正是刘恒被归划至的新写实的功绩。即便是在新写实作家脉络中,刘恒也是独特的:唯有他是从历史走到当下而不是相反。
整部集子里的作品一分为二,乡土书写中充溢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土痞气,城市书写对知识分子与中产的生存状态描摹与晚生代有着不同面目(唯李洱似之)。然而,卑琐残暴顺天委命的乡民(《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世故圆滑精致利己的现代市民(《白涡》),理想一点点被蚕食殆尽的青年(《教育诗》),又无一不是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着却终究被卷入漩涡万劫不复,苦难与悲剧背后渗出的惨痛带有浓厚的宿命感,从乡村到城市,从前现代到现代,都难以摆脱。但又被看似圆滑的精雕细琢的语词悄然抹去,如果只看见这浅表的幽默和嘲弄,终是会弄巧成拙,就近乎了沈从文自嘲的“买椟还珠”。事实上,在内容与语词一来一去的张力中潜藏着刘恒内心的沉痛和无可排解的郁闷,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他的八十年代底色来:启蒙叙述与破灭后的无出路感。也因此,刘恒本人通过文学的方式探讨“人的那种自身的弱点”并最终将之归为“命”,认为“对人的生活价值的影响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么一种作用”。
然而在我看来,很多研究者还是相当程度地窄化了刘恒“宿命论”的潜在意义。他们如其所述地通过创作谈和作品加以归纳提炼,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讨论”宿命“的指向,无一例外地最终将之指向现代哲学的一个又一个终极真理:难以餍足的欲望、作为一种存在常态的孤独以及无可回避的死亡。每一位研究人的概括都不能再好,他们无一例外都想着法子让自己的分析开出新异的花来,但终归还是隔靴搔痒。在我看来,刘恒笔下的欲望、孤独以及死其实是一个逻辑清晰的意义链条,而面对研究文献中饶有意味的对于何以倒向”宿命论“的阐述的缺失,你很难说这些学富五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的精英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真的是西方现代文论读得太多并且经过九十年代的分裂而对革命与启蒙等宏大叙事天然反感抑或是压根没触摸过史料,无论哪种情况,就我目之所及的刘恒专论而言是让人觉得悲哀的。
站在这个时刻,在回看过去的我的眼中,这些对于刘恒作品的论述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更值得人玩味的文本,或许可以做出些许肤浅的描述、轻浮的判断:这些生产于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前期的研究文献为我们揭示了研究者脑海中的一个与对于互联网的美好预期类似的乌托邦式的现代性泡沫。它充斥着人们对革命、启蒙话语的否定与拒斥(即使不是直接的也必然是潜意识中的),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已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里,上世纪中叶已降的历史不是已经离得太过遥远就是在脑海中对之完全没有认识——一句话,已经成为一场再也不可能复现且让人觉得恍如隔世的噩梦,留给我们的只有美好的明天:看看我们腾飞的经济,屹立不倒的经济,作为整个世界增长引擎的经济,我们再不会回头了!
我承认自己提供的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尚待严密的事实与逻辑论证,但我想在这个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这批论述本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这样一个事实——至少也是一个事实的侧影。这其实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至少在我所读到的研究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专著与出版于这一时期中的非文学类书籍中,这一状况真实存在着。这种源于时代的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不仅充斥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同样存在于我的父母、亲人、老师、同学,几乎身边的每一个个体身上。从九十年代以来畸形生长的社会成为滋养这种乐观主义的温床,时间越是向后就越是繁茂,而它越是繁茂就越是使得与时代不协调的音色被挤压覆盖:人文主义大讨论、新左派右派之争、断裂、盘峰诗会层出不穷的知识分子闹剧随着这一群体自身的被驱逐而迅速边缘化;红色文化、民粹主义、国家意志一次次回潮但始终成不了气候;只有王朔、被误读的王小波、郭敬明、韩寒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自成这条路径中唯一持续闪烁的一脉。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就是在被挤压的声音之中也同样存在着声音大小的差异,存在着一声压过另一声的事实,存在着釜底抽薪的危机;更不用说所谓的被挤压这一行为本身自始至终都不过是被挤压者里的一方所主动主导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此一阶段刘恒研究中一再重复的无涉现实指向的本质化论说(说到底这些精英也没真的服膺于解构神话)就不再全然是中性而无可指摘的。况且,这种论述自身也始终是未完成的。
周保欣指出“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要件的不足,构成了日常生活苦难的一种现象性起源”,而“在贫困的生活重压下,自我的生存就是贫困者最根本的道德,其它的道德理想都只能屈服于这个最大的道德,接受着它对人性、对理想道德形式的改写。”因此,恶就“和人性善恶起源无关”,它“是被动的恶,是贫困对人性的压抑和对理想伦理形式的摧毁”。这提供给我们一个整合现有论述的视角:如果将人物的死亡(通常是非正常的)视为刘恒写作中整个链条的结局,无论是食、性的欲望还是难以排遣的孤独都只是绵延冗长的链条的中段,而“匮乏”其实才是造成这些难以逾越的生存困境的一个更具本质性的原因(我知道自己有陷入本质主义之嫌,不过我自己也并不信任完全的解构真的能带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所以还是暂且妥协吧)。无论是难以满足的食欲、使人性沦丧的性、对于金钱、权力无止境的追求还是为了逃避难以排遣的孤独而走向死亡,都源于人对匮乏状态的恐惧。正是因为对匮乏的感受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才使人即便伤天害理丧失人性也要追求满足。而在这追求满足的过程中悲剧也就一次次上演着,它不仅发生在被掠夺者身上也同样发生在掠夺者的身上,换言之,在匮乏状态下,掠夺者看似作为施暴的一方,实际上是他在掠夺的过程中也悄然丧失了自己原本具有的东西,而这种丧失可能比他所得到的要多得多。以《伏羲伏羲》为例,杨金山因为对无后的恐惧而对菊豆施暴,但每一次为了延续后代的施暴在结果上却都使自己离原本的目标更远;而在杨天青那里,对于性的渴望和不得的事实则促使他一步步走向错误的轨道,即便最终如愿以偿,也不可挽回地使他陷入伦理道德的困境之中。
实际上,这种源于匮乏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显现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作品里:《活动变人形》中静宜与倪吾诚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九月寓言》中饥饿作为匮乏的变体所带来的苦难令人触目惊心;《长恨歌》中王琦瑶与《繁花》里众人的孤独同样是源于人与人之间真正可延续的“爱”的匮乏,只不过这里的匮乏更多源于”对人的生命力的压抑,对正常人性的禁锢和摧毁,以超越性的神圣理念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肆意颠覆“。写到这里,问题的关键终于呼之欲出:如何看待这种匮乏?这才是此期刘恒研究中始终处于空缺位置的关键问题。周保欣极富洞察力地指出:新写实的“许多作品中,生活是如何苦难的,是什么让生活变得如此苦难的己经变得不是十分重要,而苦难状态下的人性展示才是作家迷恋和用力展示的重要部分”。而在本应填补作者未能完成的空隙的研究者那里,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被提出过,即便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周保欣也选择将之悬置,似乎呼之欲出就是他所要追求的最终效果。至此,所留给我们的就不再只是单纯的一个“为什么”,而成为一连串令人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作家们不再关注造成生活苦难和匮乏的原因?为什么研究者们甚至对这样的缺位毫无意识?为什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也放弃了就要到口边的追问?这种匮乏及其所造成的存在状态今后是否仍将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日常现象?有没有方法解决它?又愿不愿意解决它?在我看来这种震耳欲聋的空缺才是令人惋惜的。
这空缺也令那个在研究者口中一而再再而三争论不休的问题重回我们的视野:究竟该如何评价刘恒九十年代的转型?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所有在中国长期写作并介入文学场的作家(见附录二)。但显然,它与“如何评价先锋作家九十年代的转型”这一个问题的关系更为密切。一般而言,九十年代炙手可热的批评家都认定同样在这一个时代炙手可热的先锋作家们的这一时期的创作是一种深入和进步,但我始终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文学场态势的复杂性尚待客观梳理,其中形成的或大或小或远或近的利益集团尚未廓清(即便最终证实他们不是有意为之,但客观上却绝对存在,这与当时的文学生产机制关系密切),更是因为现有的关于这一阶段的权威性研究表述与非权威性表述(当时“在场”的九十年代批评和现在开始“返场”的九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大多数正是在这些批评家的手下建构完成的,当一个人同时“垄断”了描述与评价的权力你又怎么能够对他的言说完全信任呢?刘恒虽然并非先锋作家,但其早期创作更繁杂,态度也更近先锋,而且因为频繁的影视改编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效力,而更受瞩目。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路径与余华相似,所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回退和态度上的放松,因此与同为新写实出身的刘震云形成截然相反的发展路径(九十年代的刘震云实际上有些回到形式的意味)。郑乃勇道出了最为朴素的感受:“九十年代的刘恒对现实显得过于宽容乐观了,甚至还有点含情脉脉,将苦难的困境戏剧化、幽默化,更是使苦难困境丧失了给人物和读者带来自我感动和道德审判的可能,它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必须经历的环节,成了现实得以展开的依据,成了存在的基本内容。”这又一次让我想到余华的《活着》。
面对这样的“转型”,周保欣倒是没有选择和稀泥,他剖析了其中的潜在影响因素:新写实“过度关注自我境遇,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苦难叙述没有超越性,而在于作家那种即时性的情感色调和注视苦难的目光会随着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个人过上衣食不愁、甚至是锦衣玉食的生活时,我们的苦难意识亦随之会被各种新的趣味所填补,不再看到身边正在发生的苦难。不幸的是这己经成为我们的文学事实。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作家们收入渠道的多样化,版税、影视编剧、改编、专栏写作等,让许多作家迅速脱贫致富,很多作家对叙述普通人的生活苦难早已变得兴意阑珊。作品的市场份额、大众趣味、白领文学、黑夜的纵情与狂欢等等新的叙事法则,早己取代了新写实小说时期作家们那种集体关注凡俗人生苦难的叙事欲望。更为甚者,在有限的叙述社会弱势群体苦难生活的作品里,有些作家也失去了早些年的愤怒和怨恨,不是如鲁迅所说的‘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以有闲阶层的悠闲、把玩、品赏姿态,在对他人苦难的叙述中寻求一种刺激和美感。这不能说不恶劣。”也许声音确实尖锐了些,但我想正因为尖锐才有其价值和意义,况且又怎么能说他没有道出事实呢?
最后加两个附录:
附录一:从欲望角度看刘恒的性书写:
在这种情况下看待刘恒笔下的性欲和当代人的性变态问题似乎能够得到一个解释:在性的放纵上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摆脱秩序与规训的选择。之所以用性来表达这种对生命激情与自由憧憬的向往不仅由于它本身就是人不可回避的生理需求,更由于唯有在性带来的高潮与纯生理性快感中,这种生命意志才能得到最恣意的绽放。性的象征意涵正在于此。而人物越是陷入性无法自拔越显示出他在生存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压抑的深重,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往往是最底层的女性被刻画为欲求不满者(更确切地说是提供了一个看待这些现象的视角),为什么又是最穷苦的男性身上充溢着暴虐和近乎变态的性欲,如此换用到《伏羲伏羲》中,就可以理解杨青天和菊豆之间的欲望关系了。但性欲在使得人释放自己被社会压抑的生命力量的同时又更为深重地,同时也是吊诡地被压制着。从这个角度看,在社会层面中存在的对性的污名化实际上又成为社会规训机制的补偿措施,在短暂的释放后施于人更深的道德谴责。正因如此,杨青天与婶子之间的情欲反过来又受到压抑,最终带来悲惨的结局。而作者对此的细致描摹与悲剧性演绎,显示着他的态度,这态度本身又同那个时代紧密相关,批判性由此可现。附录二:关于青年作家考编的一个看法:
如果你看了我关于晚生代作家的一系列文章自然就能很好地理解。我一再强调的是中国在世纪末的文学场中形成的短暂的边缘空间是民间文学场的绝唱,其后来所演化为的三元格局(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与学术主导详见曾念长博论)里再不存在一个能够容纳如此空间的位置。“断裂”事件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和其速朽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场的一个预演,它的完全落幕才是真正的最后的“天鹅之死”。看看这一批人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如何遭到埋没和掩盖就知道了。更不用提现如今的环境。如今这番暂时过去的热议只不过是经由已死腐尸借尸还魂再演罢了。
事实上,即便这些青年作家不考编也终将面临着被体制接收的问题,从余华苏童到朱文韩东再到如今的班宇双雪涛,政治场永远强势存在永远逼迫人做出选择。我想这话说得还不够准确,事实是:他们从来都没有选择。
当然,有必要打个补丁:我所说的没有选择和不再存在并不意味着作家就不能再写出来有批判性的作品,这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而且事实上加入作协之后的作家也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但你要知道的是,在 bigbrother 的注视下写的作品永远与民间独立空间里的作品崭然有别。
参考文献:
【1】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2】昌切:《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刘恒的启蒙叙述》,《文学评论》,1999 年第 2 期。
【3】周保欣:《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4】郑乃勇:《生存困境的逼视与抚摸——刘恒小说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