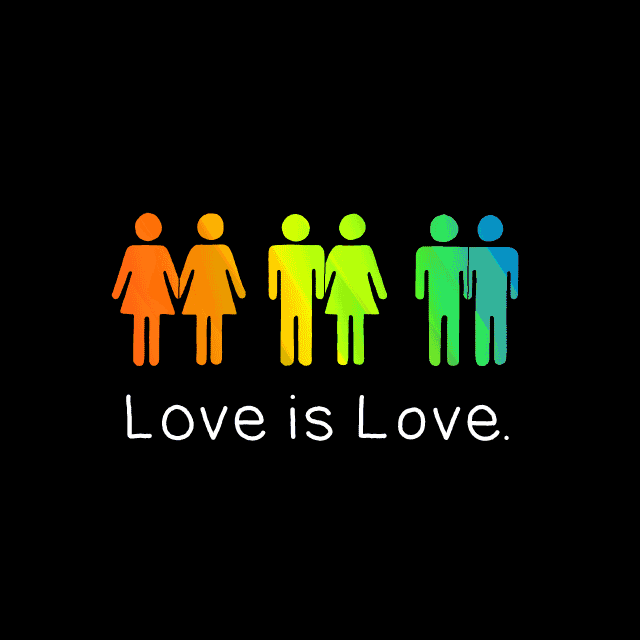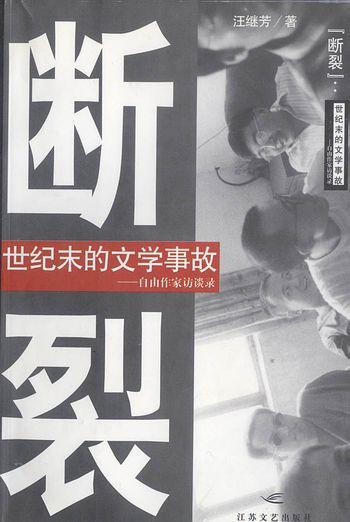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活动变人形》读后:在审父与自审之间
许子东认为“王蒙似乎用钱钟书式的夸张嘲讽笔法在处理张爱玲的灰色小市民故事,七巧性格的各个矛盾侧面正由三个不同女人的不同悲剧细节而分别演化”,并将细节的刻画视为“林海音式的童年回忆和老舍式的京味生活碎片”,指出它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为数不多可以和其他现代文学经典对话的长篇小说”(主要是《围城》《金锁记》)。并且认为由于孩童(倪藻)视角的加入(实际上也就是学界常言的“审父”),使得原本的人性视角下的病态转换为社会历史的病态。
说得更明确些,似乎可以认为这里存在着一种转换:从启蒙视角转向革命视角。实际上这里存在另一个容易遭到忽视的问题:倪吾诚从来都是在倪藻眼光之中呈现出来的,因此,对他的批判、否定和同情、赦免都是在服膺于革命者的视角下看到的蜕变时期的知识分子灵魂的痛苦的写照,这不可避免地使得倪吾诚的形象与“真实”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这是革命对启蒙的反观过程中所必然存留的。王春林在《王蒙论》中的表述十分具有代表性:“王蒙站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毫不犹豫地宣告了启蒙知识分子倪吾诚的死刑。很显然,在他看来,要想依靠启蒙来拯救中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与启蒙相比较,唯有自己所坚决认同的革命,方才可以被视为中国的真正福祉之所在。”
饶有意味的是,郜元宝很快对此加以“反驳”,他将倪吾诚放置在魏连殳、吕纬甫、倪焕之这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零余者”)之中加以比照,指出王蒙并未像鲁迅、叶圣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体己”,疏离的理性化审判使得倪吾诚不仅与魏连殳们拉开了距离——他只是一个“成色不足的赝品”,更使得作者所占据的立足点变得不那么可靠:作为审父发起人的倪藻自始至终都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他不能也无力对之做出真正的审判。除此之外,在作品被完成的八十年代,对启蒙热情洋溢的复归又怎么会引发出对启蒙的冷眼审判呢?郜氏对这样一个事实所作的轻描淡写却又极为重要的描述自然成为难以驳斥的辅证。由此,他提出全书的主题应该是“以四十年代日据时期北平倪家的悲剧来显示现代文明要在古老的东方古国结出美善花果将会何等艰难,或者说是为了显示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的尴尬,以及古老中国实现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的任重道远”。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澄清也有其必要性。
“零余者”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最终身份归属,但倪吾诚与那些几十年前就被创造出来的同僚们相比,终归还是更为特殊一些,除了在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之间徘徊不定之外,他同样是“革命”的“零余者”:“在‘革命’的征途中,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一生拥护革命,追随革命,但并未弄清‘革命’的真正内涵,也未为‘革命’做出过有意义的事。”他的人生揭示出了一条知识分子从启蒙转向革命的路径:在启蒙时代的失意者不假思索地拥抱革命以至于在“偏狭与激进使革命误入歧途”(见夏义生)。这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审中国革命的视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钱老指出的:良善的愿望为何在落实的过程中最终演变为难以承受的苦果。
更值得关注的还有郜老师提到的反思和审判中存在的双重标准问题:“倪吾诚和静珍、静宜都一直活到了七八十年代,他们和成人倪藻的政治生涯至少有二三十年的交叉。在这段时间里,倪吾诚、姜静珍和姜静宜难道不也见证了成人倪藻的政治生涯和成人倪藻的新的时代的同样的荒诞与悲惨吗?为什么王蒙只片面地浓墨重彩地描绘他们几个在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没落生活,而仅仅在《活动变人形续集》里那么匆忙、那么零碎地交代完这三个人在 1949 年以后的二三十年的生活呢?”王蒙本人意识到了这种双重标准,甚至他之所以要引入新的时代和续集就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在“审父”的同时完成“自审”,许子东指出这建立在一种“微妙的反讽布局”之上(倪藻通向革命的最初时刻紧跟着的却是一大片对于革命失败的叙述)。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王蒙最终放弃了自审并且对自己的“审父”如此义无反顾?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张承志那里,甚至在韩少功的笔下也多少有所流露。确实,无论是“少布”还是知青、红 WB ,对他们而言,那些最苦痛的岁月同样凝定了他们青春的美好年代,即便再深重的苦难,在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那里苦难都迟早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蜕变为确证自身高尚的证章,这一点从那些流溢着青春无悔呐喊声的文字之中很容易体会到。甚至这种高扬的激情会影响现如今的我们——一个又一个远离了那个时代甚至毫无理想主义追求的年轻读者们。问题在于,这种共情本身难道不会是又一个表面温情脉脉实际危机四伏的陷阱?在高呼着的无悔背后所隐藏的难道不是另一种对真实自我的放逐?追问到底,王蒙们究竟是否有资格自命为不可一世的“审判者”(难道我们就有吗?),他们对青春中污秽有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当然不是完全如此)难道就不是与他们所审判的那些人一样甚至更为恶劣?这是否就是他们无力也不愿面对当今时代里更难以忽视的歌哭的原因?
可能还是我看的文献太少,但我还是感到没什么人愿意多谈一谈姜氏母女三人(如果捎带上倪萍和三妹,那就是五人)。绝对善良且塑造单薄的倪藻就不说了,倪吾诚尚且有其可怜之处和优点,但王蒙笔下的女性似乎就是恶的化身,罪的渊薮。我可以理解塑造一两位纯粹的可恨女性,将之同男主角们相比较,从而揭示传统的问题平等地存在于男女两方身上,甚至对女性压迫得更为严重。但实在很难理解,自始至终所有出场的女性都是负面的,即便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赵慧文也很难称得上是符合“新时代”定义的女性。虽然当代作品读得不够多,但是在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男性作家的笔下确实很少能够看到符合主流历史叙述口径的女性。我想之后自己将不再多提这方面的不满,而更自然地将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自我意识压抑作为一种常态。完整且决绝的祛蔽终究只能经由个体的体验而非言说和所谓的“理解”。
参考文献:
【1】夏义生:《倪吾诚: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双重“零余者” ——— 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当代文坛》,2011 年第 1 期。
【2】郜元宝:《审视或体贴 ——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文坛纵横》,2019 年第 5 期。
【3】郜元宝:《未完成的交响乐 ——<活动变人形>的两个世界》,《南方文坛》,2006 年第 6 期。
【4】许子东:《重读<活动变人形>》,《当代作家评论》,2004 年第 3 期。
【5】王蒙:《关于<活动变人形>》,《南方文坛》2006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