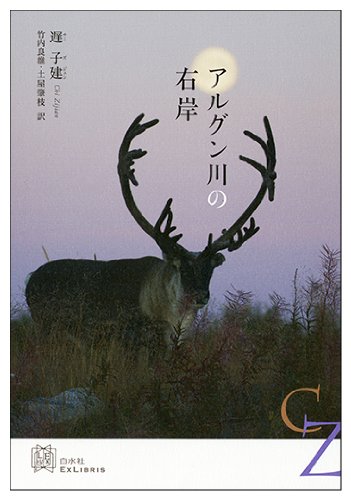烘衬“鲜花”的“绿叶”——从三个次要人物看《哈姆莱特》
如果将哈姆莱特看作是这座由莎士比亚所构建的悲剧花园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绚丽花朵,那么剧作之中的其它形象就是烘衬出他鲜艳色彩的幽幽绿叶,他们用着这样那样的方式将这位忧郁却又闪耀着人格光辉的王子突显于文学的万花园之中,然而回顾他们自身,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绿叶”身上也蕴含着无尽的韵味。本文试图通过对《哈姆莱特》中霍拉旭、乔特鲁德以及奥菲利娅这三位相对次要人物进行分析以此来简单谈谈自己在阅读这部旷世杰作之后的一些感受。
1. 霍拉旭:友人还是“恋人”
这大概是在读完《哈姆莱特》之后最令我好奇的一个问题,在剧中,作者对于霍拉旭的定位是哈姆莱特的“好朋友”(第一幕 第二场),这一点可以十分明显地从二人的对话以及行为举止中体现出来,但在笔者看来,两人的关系似乎又不似莎翁所写到的那样简单。在剧作之中,被哈姆莱特称之为朋友或是以朋友之礼相待的人除了霍拉旭以外还有马西勒斯、勃那多以及儿时玩伴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然而在这些“朋友”之中,似乎只有霍拉旭得到了哈姆莱特的重视,这是他与众不同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要想更好地理解二人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首先要探寻霍拉旭本人的情况。通过两人的交谈我们可以得知霍拉旭是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读书时结交的好友,从这一点来看二人相遇相知的时间似乎并不很长,但为何并不长久的友谊却显得比自儿时依始的情谊更加珍贵甚至是坚不可摧?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是二人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抑或说精神追求之上的。众所周知,德国的威登堡大学正是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的重要阵地(1517年10月31日,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上面阐述了他对罗马天主教会兜售“赎罪券”的看法,掀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而共同就读与此的二人也因此接受了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精神在哈姆莱特那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霍拉旭这里则通过他学者的身份以及他谈吐之间所透露出的充分学养中体现出来。正是在这种精神上的共鸣的影响下,二人之间的友情得到了巩固。
其次,霍拉旭性格之中的忠诚勇敢以及对于友人的关爱亦成为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当鬼魂再一次出现,哈姆莱特执意要跟随它的指引而去之时,不似同样在场的马西勒斯,霍拉旭用更加关切的言语劝告着失神的王子:“要是它把您诱到潮水里去,或者把您领到下临大海的峻峭的悬崖之巅,在那边它现出了狰狞的面貌,吓得您丧失理智,变成疯狂,那可怎么好呢?”当哈姆莱特经受游魂的惊吓而显得疯疯癫癫之时,霍拉旭也是尽心地用平和的话语安抚王子的心灵。自始至终,霍拉旭遵守着他对哈姆莱特许下的承诺,并且在各种场合极力地配合着心力交瘁的王子的行动,而相比之下,罗森与吉尔二人对哈姆莱特种种行为为就仅仅是打着友谊的幌子的自利之举。
除此之外,对于哈姆莱特而言,在那样一座“长满了恶毒莠草的荒芜不治的花园”,布满了监视自己的线人的“最坏的牢狱”,他的身边也只有霍拉旭一人可以成为他倾诉与寄托的对象。如果说霍拉旭本人所表现出的品质以及他同哈姆莱特之间的契合之处为二人的关系提供了可行性,那么这一点则为哈姆莱特提供了选择的必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人之间才能形成蕴含着精神、战友以及主臣三种关系纽带的珍贵情谊。
纵观整部剧作,霍拉旭的存在不仅为哈姆莱特的复仇行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协助(在戏中戏《捕鼠记》中他帮助哈姆莱特观察克劳狄斯的表情,在他从英国归来时霍拉旭帮助王子递送了信件并且前去接应等。)而且为经历了父亲的暴死,叔父的篡位,母亲的乱伦,恋人的疏远,好友的背叛等一系列事情而感到前途渺茫,孤立无援,甚至想要让自己“坚实的肉体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的王子提供了一种来自精神上的支持。并且当我们跳出两人的关系去理解霍拉旭就会发现这位平易近人的学者对于整部剧作的情节发展实际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戏剧中的其他人物是树叶的话,那么霍拉旭在戏剧中就是将片片树叶连接在一起的树干。他是整部戏剧中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不着痕迹的引出人物对话与情节,将碎片化的剧情拼凑起来,作为情节与情节之间的关节一步步地推动着情节发展,增添了戏剧的可信度与完整度。
回到最初的问题,总而言之,从文本的表层内容来看,霍拉旭与哈姆莱特之间的关系主要包含了知己关系、战友关系、君臣关系三个层面,而三个层面在融合之后则形成了一种超越普通意义上的友人关系。笔者此前在查阅有关《威尼斯商人》的文献时发现有些研究者将安东尼奥解读为一位“对同性具有爱恋之情”的人,这体现在他在涉及到巴萨尼奥时的种种行为之中。那么同样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形象,哈姆莱特同霍拉旭之间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关系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从此前所给出的例子来看,在言语组织方面霍拉旭与哈姆莱特二人均不存在超出自己身份与关系的表述,并且不同于《威尼斯商人》中大量的侧面证据,在《哈姆莱特》中莎翁也并未从侧面对二人进行刻意地书写,而最为有力的证据就是哈姆莱特行将就木之时对霍拉旭所说的话语:
“(哈姆莱特)……霍拉旭,我死了,你还活在世上;请你把我的行事的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解除他们的疑惑。
(霍拉旭)不,我虽然是个丹麦人,可是在精神上我却更是个古代的罗马人;这儿还留剩着一些毒药。
(哈姆莱特)你是个汉子,把那杯子给我;放手;凭着上天起誓,你必须把它给我。啊,上帝!霍拉旭,我一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要永远蒙着怎样的损伤!你倘然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1]
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哈姆莱特之所以阻止霍拉旭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希望霍拉旭传诵自己的事迹,保留他的名誉,而且从其语气(“要是”到“损伤”一段)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纯粹的利己行为,倘若二人之间的情感超越了友谊,那么在哈姆莱特濒死之际定然不会用这样强硬的语气。
综上所述,霍拉旭同哈姆莱特实际上仅仅是亲密的友人,同时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哈姆莱特》已经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在对霍拉旭这一人物的塑造方面仍旧有着某些遗憾(即人物性格并不完善)。
2.女性:王子悲剧的悲惨陪衬
如果说霍拉旭是整部剧作之中同哈姆莱特最为亲近的人,那么奥菲利娅还有乔特鲁德这两位女性则是我们这位郁郁寡欢的王子的悲惨陪衬。
女性主义莎学研究者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莎士比亚具有女性主义倾向,她们声称他的作品描述了“完美”的女性形象,而且这些形象意识中的超前性恰恰是莎士比亚女性主义意识的反映,而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关注更加印证了莎翁的女性主义情结,所以他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原初女性主义者”[2]。另一部分评论家则完全不同意上述观点。在她们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男性所作,而所有的角色也皆由男性扮演,所以他的戏剧中不可避免地弥漫着男权主义意识甚至可以说他的剧中充斥着对男性的尊崇和对异性恋的肯定,弥漫着厌女主义的气氛。[3]这两种说法各有其根据,但在《哈姆莱特》一剧中,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具合理性。
在剧作的前期(准确的说是在第一幕第二场国王的婚礼之后),哈姆莱特就已经说出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这样的论断。这句针对他的母亲——乔特鲁德的话通常被看作是哈姆莱特厌女主义的最佳证据,而其背后的原因似乎正如歌德所言:“他受到的第二个打击把他伤害得更深、折磨得更重。那便是他母亲的结婚。”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新婚)同父亲的死一起形成了他对母亲的仇恨,此时哈姆莱特眼中的乔特鲁德似乎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慈祥和蔼的母亲,而是一个性意味上不坚定和软弱的“急不可耐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的丑恶女子。
这种仇恨的情绪不断地在哈姆莱特的心中滋长,在父亲的亡魂告知他事情的真相之后达到了顶峰,当他后来不分青红皂白分地对乔特鲁德发泄这种愤怒之时才知晓自己的母亲对克劳狄斯所犯下的恶行毫不知情,然而却已为时已晚,正如乔特鲁德所痛呼的:“啊,哈姆莱特!你把我的心劈为两半了!”王后已经遭受到了身体与情感上的沉重打击,以至于悲痛难耐。在笔者看来,尽管她在某些层面上确实有所过失,但并非罪大恶极以至于要承受来自自己所心爱的孩子的沉痛指责,在这个意义上,哈姆莱特本身也成为了乔特鲁德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当我们走出哈姆莱特的行为进入乔特鲁德的视域则会发现,不似哈姆莱特对待她的恶劣态度,这位可悲的女子在举手投足之间都关心着自己的孩子:她不仅掩盖了哈姆莱特杀死波洛涅斯的事实,而且替他饮下了那杯致命的毒酒[4]。这些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正深刻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于命运和伦理的屈从与认同,因而乔特鲁德是脆弱的也是可悲的,她是带着一种世俗观念下的悔恨与内心深处的矛盾而走向了毁灭,同时,正是她的离世在某种层面上才最终促成了哈姆莱特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死又显出一种“陪衬”的意味。
与乔特鲁德一样,奥菲利娅也是哈姆莱特口中“脆弱的女人”之一,然而相比乔特鲁德的仍有一定缘由,她的死亡则是一种更加典型的伤及无辜的表征。
诗人兰波曾在《奥菲利娅》中为她写下这样的诗句:
“因为四月的一天清晨,一位英俊苍白的骑士,
一个可怜的疯子,默坐在你的膝下!
苍天!爱情!自由!这是怎样的幻梦啊,可怜的痴心人!
你融于他,就像雪融于水;
你伟大的幻梦窒息了你的言语,
——而可怕的无限又使你的蓝眼睛惊慌失措。
——诗人说,你在长夜的星光下,
来找寻你采撷的花朵;
说他曾在水上看见,枕着长长的纱巾的
洁白的奥菲利娅随风飘动,像一朵盛大的百合。”[5]
她确实如同洁白绽放的百合,纯洁而又美丽,然而使她染上淤泥与血污的却是那个她所深深爱慕着的昔日情人。为了自己的复仇大业,哈姆莱特残酷地亲手摧毁了他与奥菲利娅一手构筑其起来的爱情,听听这位“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怎么羞辱他曾经爱恋的人吧:“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算了吧,我再也不敢领教了;它已经使我发了狂。我说,我们以后再不要结什么婚了;已经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以外,都可以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再结婚,进尼姑庵去吧,去。”如果说奥菲利娅仍能够在夕日海誓山盟之人这样突如其来的恶意中伤下挣扎着生活下去,那么当自己的父亲也因为这样一个男子而溘然长逝之时,这颗孤立无援的心就已经难以经受重负,最终只能走向癫狂了。
然而即便如此,她的悲剧还没有结束,最令人痛心的也正是她的死亡,在那之前她还手持着花环怀念着曾经的爱人:“这是给您的茴香和漏斗花;这是给您的芸香;这儿还留着一些给我自己;遇到礼拜天,我们不妨叫它慈悲草。啊!您可以把您的芸香插戴得别致一点。这儿是一枝雏菊;我想要给您几朵紫罗兰,可是我父亲一死,它们全都谢了;他们说他死得很好——(唱)可爱的罗宾是我的宝贝。”总的来看,奥菲利娅的人生悲剧在某些角度看就是由哈姆莱特一手酿就的,这位姑娘的离世只能称作是哈姆莱特的陪葬亦或是说一个注脚,正如海涅对他的评论:“这便是弱者的灾殃:每当他们大祸临头时,首先便在他们所占有的最好的、最珍贵的东西上发泄。”[6]无论是前文所述的乔特鲁德还是这里的奥菲利娅都是如此。
笔者认为,透过奥菲利娅的悲剧可以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无意识的揭露,它客观上体现出父权主导下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以及她们对于自身命运的无能为力,这是极不公正也极不合理的,同时,作者也表现出对在哈姆莱特身上所体现出的当时社会上所普遍具有的极端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个人主义行为的批判,在以上这两个层面上可以认为莎翁已经跳出了对于个人的考量而升华到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悲剧的观照与思考。
参考文献:
[1](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吴兴华校,《哈姆莱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158页。(本文所引《哈》剧原文均出于此)
[2]原初女性主义者指的是在女性主义运动发起之前同情女性境遇并支持女性通过反抗来达到改造社会之目标的人。原初女性主义者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3]王玉洁,《莎士比亚:原处女性主义者还是厌女主义者——莎士比亚女性观探佚》,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李安定在《两位悲剧女性陪衬下的残酷王子——哈姆莱特》一文中指出此处的饮酒实际上并非“误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原因如下:
首先,报告奥菲利娅死亡的一段情节是由王后告知的,这种由使者或宫人就可完成的任务却是王后来传递本身就显得有些蹊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段场景是这样与设计毒死哈姆雷特的场景衔接的: “(国王) 当他口干舌燥,要讨水喝的当儿,我就为他预备好一杯毒酒,万一他逃过了你的毒剑,只要他让酒沾唇,我们的目的也就同样达到了。且慢,什么声音?”此处实际上是先有了可疑的声响,然后王后才出现,这样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断,王后很有可能已经听到了两人的密谋。但她又为何不去戳穿他们呢?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是因为她并没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她虽然听到了二人密害的想法但此时克劳狄斯已经十分明确的加强了对哈姆莱特的戒备,作为一向关心孩子的王后,她的一言一行自然难以逃脱克劳狄斯的监控;另一方面此前同哈姆莱特的交流也使她的内心受到了审判,受辱失节与违逆不道令她自觉难以存留于世间,为了赎罪她甘愿替代儿子走向死亡,但从“请您原谅我”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她本人对于克劳狄斯已经产生了情感,因而这一举动就显得格外凄凉与悲恸。
[5](法)兰波著,王以培译,《兰波作品全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5页。
[6](德)海涅著,温健译,《莎士比亚笔下的女角》,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jpg)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