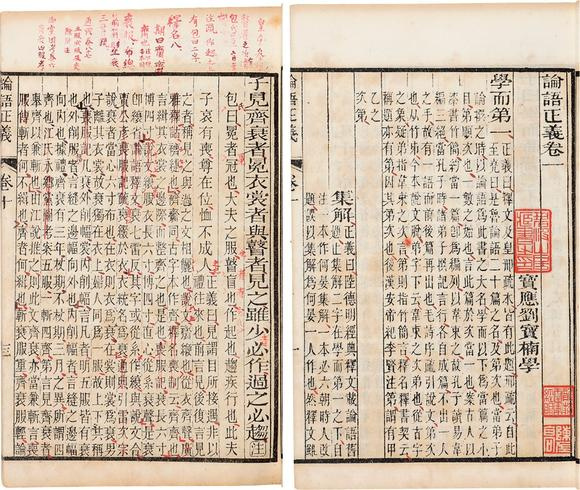从“荒诞”到“反抗”——论加缪《局外人》《鼠疫》主题之变
【摘要】 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加缪在通过文学形式表述自身思想时注重采用“哲学思想的文学主题化”的方式,这使他不同时段创作的文本被赋予了不同的哲学内涵。他在《局外人》和《鼠疫》中分别通过默尔索、里厄两个人物揭示出小说的不同主题——“荒诞”和“反抗”。默尔索的意义更多是为了揭示此在个体身处于“荒诞世界”这样一个现实,里厄及其行为则为个体如何在荒诞世界中自处提供了“反抗”这个解决方案。反抗意识及其行为的悲壮性正体现了加缪对人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肯定。
【关键词】 反抗、荒诞、默尔索、里厄
1957年,瑞典文学院以“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1]为题词,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给了年仅44岁的法国文学家加缪,而于1940年和1946先后完稿的《局外人》和《鼠疫》则成为奠定这位“年轻作者”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地位的两部扛鼎之作。即便加缪本人多次公开声称自己并非哲学家,甚至并非存在主义哲学家,其作品中所显露出的鲜明哲学底色还是揭示出他“具有明晰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作家”这样一个复杂身份,而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正是其作品中文学性与哲学思辨意味的“水乳交融”。笔者认为,加缪作品中呈现出的这种“哲学思想文学化”的特点是使我们得以把握其存在主义思想的演变进程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局外人》和《鼠疫》这两个文本的分析,来尝试梳理加缪“荒诞哲学”的发展和转变状况。
一、哲学理念的“文学主题化”
在作家进行特定文学文本的创作时,通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分配文学性要素与非文学性要素在文本中的占比和定位”,这里往往会涉及到的是作者如何处理形式与主题二者之间张力关系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作家会根据创作中的具体情况来这两种要素进行处理,手段之一是采用不同的文体对之加以划分界定,例如说理型散文通常更侧重对非文学性要素的呈现,而诗歌和小说则是更注重文学性要素的文体形式。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当下的文学观念是文学本身在历史进程中长期演变发展所逐渐生成的,在漫长的文学史历程中,不同文体的杂糅催生出不同的“文学景观”,以纯粹理性为代表的科学观念与以对世界进行感性认知为主的文学之间看似有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但也并非无从沟通,除了说理型散文之外,发轫自18世纪欧洲启蒙文学的哲理小说亦提供了一座可以衔接二者的“桥梁”。
当启蒙哲学家以天赋人权、理性为理论武器反对君权神授,批判封建制度,试图建立以理性作为最高价值原则的“理性王国”时,如何将在当时看来颇难宣扬且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哲学思想传递给广大的平民百姓就成为启蒙思想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的目光由此投向了具有广泛受众基础的小说文体,因而以《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爱弥儿》(卢梭)为代表的书信体哲理小说很快发展为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潮。
启蒙思想家在创作时通常“把自己的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一系列观点融进作品之中,或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或自己直接加以阐发”,因而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教育目的,同时他们也注重“运用人民的语言,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争取艺术民主化”,使作品更好地起到启蒙大众的作用[^2]。从结果看,18世纪启蒙文学中的哲理小说确实完成了将“用以解释世界的、抽象的、普遍的、理论的”哲学和“用以描绘世界的、形象的、具体的、经验的”文学统合疏通的任务。但这种“疏通”仅仅停留在“完成”阶段,由于启蒙作家对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过度强调,致使哲学思想往往难以与人物形象相协调,从而令大多文本带有浓厚的说教色彩[^3]。即便哲理小说有其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它还是为如何处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提供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循此路径,进入二十世纪上半叶,与哲理小说诞生背景相“类似”[^4]的情况再度出现在法国这个文化中心。存在主义思想家在论述自身哲学观念的同时十分自觉地将目光转向了文学,正因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存在主义作家同时是哲学家或具有明晰哲学观念的思想家,他们或是通过小说或是通过戏剧的形式来为相较难以理解的哲学思想“赋形”,从而完成传播和宣扬自己思想的目的,加缪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考查《局外人》和《鼠疫》,我们不难发现存在主义文学文本在对作者本人哲学思想的处理方式上呈现出与哲理小说截然不同的面貌。如果说书信体哲理小说的创作者们在对文学性要素和非文学性要素的取舍中更注重的是后者的话,那么存在主义作家无疑显露出对文学性的高度重视。以加缪为例,在他这里,哲学思想不再以长篇大论的教谕式文字面貌出现,它成为了更为内在的文本要素——主题。这样一种设置使作者在创作时获得了更多的灵活性(但也还是有限的灵活性),他仅仅需要围绕着自己所意欲表达的观念来展开故事,而不必让人物完全沦为自己观念的传声筒,正因如此,存在主义文学文本显示出了诸多样态而并未局限于一隅。
而参阅加缪本人对哲学与文学关系的论述,则可以发现他自觉采用文学文本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承载物背后的考量。他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性表述如下:
1.“创作被视为人意识到荒诞后可能有的一种态度”[^5];
2.“伟大的小说家是哲学小说家”[^6];
3.“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只要哲学漫出了人物和动作,只要哲学成了作品的一个标签,情节便丧失了真实性,小说的生命也就终结了”[^7]。
在第一个观点中,加缪直接将对荒诞的认知(哲学思考的结果)与创作(文学行为)相连接,实际上是将作家创作的动力、基础与哲学思考过程相联系,后者导致了前者;而第二个观点则表现出他个人对于文学的评价标准:即只有具有哲学思辨意识,并将之在自己所创作的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小说家,才能被称得上是“伟大”;在第三个观点中,加缪更加强调了文学创作对哲学思想表达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哲学观念的表达离不开文学创作,并且这种创作不能仅仅浮于表面(“标签”)——而要与文学本身互相交融。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加缪本人是十分注重“文学文本与哲学思想互相交融”这样一个观念的,正因如此,“哲学思想的文学主题化”成为他在创作时所注重的一个方式,而由着这样一条“路径”延伸下去,他在不同时段创作的文本也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者而言,通过对这些文本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他自身哲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情况。
二、从“荒诞”到“反抗”——默尔索与里厄的不同指向
在开始论述之前,笔者需要先对小标题加以解释说明。实际上,默尔索和里厄之间并不存在带有断裂意味的“截然不同”,所谓的从“荒诞”到“反抗”也并非指加缪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二者之间仍旧保持着一种递进发展的关系,即《局外人》的主题更多指向对荒诞本身的揭露,而《鼠疫》则在揭露荒诞的同时提出了对待它的态度——“反抗”。这样一种变化显示出加缪的荒诞哲学正处于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与两个文学文本相对应出版的《西西弗神话》和《反抗者》这两本哲学论著正是文本所体现出的转变在理论层面的表现。
首先我们来看《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从表面上看,默尔索是一个对身边所有人事都表现得极为淡漠的人。一方面他对于母亲的态度实在是异于常人:面对死去的母亲,他无法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反而为参加葬礼而感到“有点儿烦”,在送母亲进养老院的两年来他也“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更别说葬礼尚未结束他就开始为“将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感到喜悦了。另一方面,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均保持着一种因“怕麻烦”而无所谓的态度:无论是对于玛丽的问题的长时间搁置还是与雷蒙的交往,他都没有太放在心上,也没有显示出热心,相反,他的看似随和、善解人意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的被动迎合:当雷蒙第一次邀请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出于“免得自己回家做饭”的考虑接受了邀请;当他和玛丽看到雷蒙在抽打妓女的时候,由于他“不喜欢警察”而回绝了玛丽报警的要求,这些都表现出默尔索的冷漠和“不近人情”。然而,这种表面的建构都是作者刻意为之的结果。
实际上,默尔索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也对玛丽有着眷恋的情感:他在监狱中不止一次想起自己的母亲,也不止一次想起爱人玛丽。除此之外,他也对生活保持着很强的感知意愿,正如研究者李黎黎所言,“书中这些看似毫无感情的语言,绝大部分都是默尔索对周围世界的细致观察和微妙感受。他在意每日的天气和阳光的变化,他留意路人的表情和动作,他常常悄悄欣赏旁人毫不留心的路边风景。他对外界的环境变化的敏感度比常人高出许多……默尔索如果真的麻木不仁,又怎么会有如此的情致和敏锐的心思去注意他身边的环境呢,怎么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留恋描述生活里的细微情趣呢?”[^8]确实如此,默尔索的行为无疑是怪异的,但除了读者容易关注到的对人事的冷漠之外,他在生活上的诸多细节行为往往被忽略掉了。那个用来收集令他开心的内容的剪报小本子,还有对公司毛巾的提意都揭示出他是一个“可爱”的普通人。试想,若非他确实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和人格魅力,老板又怎么会想提拔他到巴黎,玛丽又怎么会矢志不渝地追随他呢?然而,这一切本应被读者注意到的事实却因为对叙事者对“冷漠”的不断强调,以及下半部书中法律体制内人员对默尔索个人的不断“重构”所遮蔽了,在这里,前者的强调无疑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后者则更多是随情节发展而出现的,但无论如何,正是这两处对默尔索身上消极方面的人为放大,帮助小说完成了对“荒诞世界”的建构与揭露。
李军认为,加缪在文学中建构的“荒诞”主要体现为“机械惯性的日常生活与人麻木的精神状态;神秘难解、充满敌意的异己力量;人与世界的断裂疏离”这三个方面[^9]。在《局外人》中,默尔索一方面正处于机械惯性的日常生活之中:即便是母亲的离世也无法替代上司因请假的不满这样一个日常小事在他心中的位置;另一方面,默尔索身上异于常人的诸多特质也正显示出他与自己所身处的奥兰城之间的“疏离”。此外,从默尔索身上,我们还能不断地看到一种“观看”的书写,例如在第一部第二节对房间外的境况的观看书写中,本来的第一人称叙事经由观看行为在短时间内转化为了第三人称叙事,从而赋予了默尔索短暂的“局外人”身份。
更为明显的“充满敌意的异己力量”在小说中则主要是指那个将默尔索推向死亡的现代法律体制。这个本来应当是捍卫人性和自由平等的体制在奥兰却成为了致人于死地的“冰冷机器”,在整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庭长、检察长、辩护律师、记者成为扼杀默尔索的一组“凶手”,他们丝毫不注重默尔索本人的真实状况,不听取他的任何说辞,而是通过看似“客观”的现实情况和证人证言完成了对案件的判断和审理。在这里,默尔索客观实在层面的局内与主观意志层面的局外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性,而这种情境则是“荒诞”的最好体现。在这种由不得自己把握命运的荒诞世界里默尔索被送上了绞刑架。在这个意义上,《局外人》对世界本身的荒诞揭露达到了顶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鼠疫》,这个被设置在与《局外人》同样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无疑承继了前者所暴露的荒诞:在格朗日复一日对浴室收费标准的统计,老哮喘病人一粒粒装鹰嘴豆来计算时间,“矮老头”乐此不疲地向猫吐口水的行为中,机械惯性的日常生活对人的异化已经展露无疑;但《鼠疫》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加缪通过塑造里厄医生,对“如何对待荒诞世界”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加缪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反抗”。这种倾向已经在默尔索身上有所展现:他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和自觉疏离,在面对神父时激动的驳斥,最终选择平静地直面死亡都是“反抗”意识的表现,但是在他这里,这种反抗带来的结果是极富悲剧色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赋予默尔索的是“唤醒世人”的作用,他被塑造为一个逐渐觉醒的人,牢狱之灾让他从无意识消极对待荒诞世界的普通人转变为真正看清了世界的荒诞性的反抗者,但他还没来得及采取下一步行动便被扼杀了,换言之,他在被捕前通过采取一种荒谬的方式来反抗荒谬本身,但这使他只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反抗者而失去了作为觉醒者本可能达到的更高的高度,这正是他的悲剧性所在。里厄则不然,从一开始他便深知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整个世界的荒诞性,作为医生的他见过太多死亡,这使他对人类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即是“人终究难逃一死”,这样一种对“人不得不面对终有一死、人生虚无”的体认带给此在个体的正是一种虚无感,因为它毁灭了生命中任何“基本的确定性”[^10],因而加缪才声称“对我来说,死亡是一扇关上的大门。”[^11]但是在这种对此在状态的清楚体认下,里厄并没有选择与默尔索同样的疏离世人以及平静地面对死亡的降临的做法,反而带有一种极强的反抗意识。在里厄与塔鲁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塔鲁:“可是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而已。”
里厄:“可这不是停止斗争的借口。”
塔鲁:“这次鼠疫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里厄:“是一连串没有尽头的失败。”“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做这件事的?”
“我不晓得。或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在这里,对于里厄和塔鲁而言,鼠疫是他们无法选择,不能逃避的命运,但这并不能作为“停止斗争的借口”,在他们看来,反抗是他们作为“人”唯一可选择的出路,因为“习惯于绝望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正因如此,即便前方等待着的仍旧是“一连串没有尽头的失败”,他们也还是要如同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一样不断地进行着“无用功”。
加缪认为人类在“荒诞”的处境下,重要的是立足现实、生活于其中。“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12]“面对荒诞,人只有反抗才能保持对荒诞的清醒认识,以挑战的态度生活其中,承担起悲剧的命运。现实是人流放的地狱,但对于反抗者来说却是人恢复尊严的王国,存在的意义和人的尊严都将在这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通过人的选择与行动重新获得它们的地位。反抗者面对荒诞,面对不幸的命运、痛苦的现实,越是意识到人生的无意义、生存的无价值,他们越要去体验,去接受,立足现实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寄希望于上帝和未来,在选择中恢复人生之伟大,在行动中创造人生价值和意义,在反抗中获得和谐与均衡。”[^13]里厄正是这样一个反抗者,他在小说中不断地坚守着自己应尽的职责并且从未放弃过救治任何患者,这样一种行为本身是令人极为感动的,但正如整部作品结尾从他自己口中说出的那样:“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最后一本胜利的编年史……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他深知当把自己乃至整个城市的人所做的和所经受的一切放置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考量是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下一次灾难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灾难中人们所做的任何事得到改善,死亡仍旧将笼罩在城市的上空,但是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反抗行为,这使他脱离了虚无主义者和旁观者的行列,令他获得了自我存在的意义,通过“编年史”的写作,这种意义得到了延伸,即“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正是通过他的反抗和记录,才完成了理查德·坎伯所谓的“尽己所能去保证他人享有更长久更美好的未来”[^14]。这种“向死而生”的反抗意识使他超越了还没能来得及反抗的默尔索,使其形象在充满悲剧性的同时染上了“崇高”。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里厄与默尔索之间的差异正是在于“反抗”这样一种行为,从默尔索到里厄,对于“荒诞”的认知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而“反抗”也从无意识的自我疏离到坚定地践行,从个体的独善其身到集体“向死而生”式的“突围”。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尝试回答的正是“当个体明晰世界的荒诞本质后应当如何自处”这样一个问题,他所给出的“反抗”这一回答正承载着个体在面对“人的有限的存在与冷酷的世界之间的不可化解的矛盾”时所做出的抉择,在这里,因“反抗”而高扬的正是对人本身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加缪荒诞哲学的内在精髓。
参考文献:
【1】(法)加缪著,刘方译,《鼠疫》,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2】(法)加缪著,柳鸣九译,《局外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法)加缪著,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 3 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美)理查德·坎伯,马振涛、杨淑学译,《加缪》,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5】李军,《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创作实践》,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6】李黎黎,《加缪的英雄与英雄的加缪——加缪小说中的悲剧英雄》,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问论文,2007年;
【7】李军,《加缪的“荒谬哲学”及其“文学化”》,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8】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 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辞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 年版,第 526 页。
[^2]: 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83 页。
[^3]: 相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国清末“小说界革命”时出现的诸多未来畅想式“科幻”文本里。
[^4]: 这里的“类似”仅指需要通过文学文本承载哲学思想。
[^5]: (法)加缪著,柳鸣九、沈志明主编,《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 3 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7 页。
[^6]: (法)加缪著,柳鸣九、沈志明主编,《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 3 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6 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文艺理论译丛 3》,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年版,第 302-303 页。
[^8]: 李黎黎,《加缪的英雄与英雄的加缪——加缪小说中的悲剧英雄》,成都:四川大学硕士学问论文,2007 年,第 29 页。
[^9]: 李军,《加缪的“荒谬哲学”及其“文学化”》,济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05 页。
[^10]: Albert Camus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Absurd,by Avi Sagi,translated from Hebrew by Batya Stein,Amsterdam:New York,NY 2002,p.8. 转引自李军,《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创作实践》,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13 页。
[^11]: (法)加缪著,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婚礼集··贾米拉的风》,《加缪全集 3 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9 页。
[^12]: (法)加缪著,柳鸣九、沈志明主编,《西西弗神话》,《加缪全集 3 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9 页。
[^13]: 李军,《加缪的“荒诞哲学”及其创作实践》,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22 页。
[^14]: (美)理查德·坎伯,马振涛、杨淑学译,《加缪》,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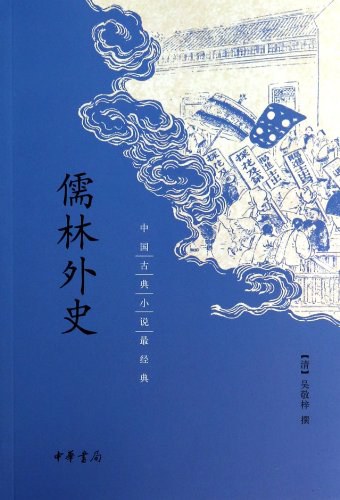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