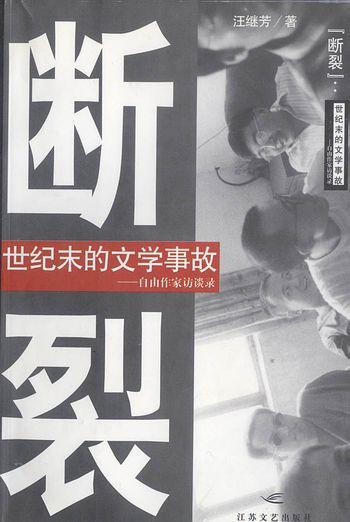九十年代的学院批评与分裂的世纪末“批评场”
【简介】 本文为鄙人本科毕业论文第二章第二小节第三部分,本节以当时批评界对“断裂”作家的不同态度,探讨九十年代文学“批评场”的分化状况,并试图为这种现象找寻某种自洽的解释。本节内容较少涉及鄙人原创观点,多参考已有研究文献,即便所参考资料甚少,所得结论亦不无问题,然则前辈学人的某些洞见,颇有思考价值,特此选录。
相较“经济场”对批评家赤裸裸的“引诱”,“政治场”的举动则来得更为隐蔽,它通过制度这个绕不过的核心要素来对“批评场”施加影响。不同于“作家场”喜于制度松动带来的“自由撰稿”可能,亦不同于“期刊场”受制度改革、“断奶”等举措影响而形成的大规模恐慌和接踵而至的“改刊潮”,“批评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更为特殊,这主要与九十年代学院批评的兴起有关。
最早提出这一定位的学者王宁认为,学院批评与直觉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一起形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三足鼎立”格局[1],而前者在大多数文学史家那里也被视为九十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大体上与以下两个因素有紧密的关系。一是对八十年代批评缺乏学理性的高谈阔论,以及“在专业研究中,过多地掺杂了自家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关怀”[2]以致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政论工具”状况的反拨。另一方面则同样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动荡有关。在此,“退守学院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而学院也被看作“逃避动荡社会的一方乐土”,“通行于学院内部的学术话语仿佛为逃避政治话语的控制提供了必要的专业掩护”[3],因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用学术话语层层包裹自身,也成为批评家的“一种思想搏击、文化反思和政治诉求”[4]。基于上述背景,九十年代的“批评场”如前所述般迅速分化,刊物编辑、文学写作者与身处学院“象牙塔”中的批评家渐行渐远,而后者在形成伊始便抱有的延续自八十年代的类似启蒙者的精英文化立场也在九十年代的发展中逐渐分裂,形成上述的诸多争辩现象。但与此同时,国家高等教育体制与教师管理体制也发生剧烈变动,据相关研究者统计,“从1990年至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数量由1075所变化为1022所;大学毕业生数从613614人变化为829833人;在校大学生数从2062695人变化为3409764人;在学研究生数从93018人变化为198885人;高校教师专任教师人数从394567人变化为470253人”[5]。八十年代的诸多批评家本就挂靠高校、研究所等机构,在九十年代他们已然成为“学院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此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高校教师,尤其是研究生数量的迅速增长,无疑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批评场”向学院倾斜(文学期刊编辑在当时仍然有编制,人数有限;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九十年代,“学院批评”在原本就具有优势的情况下搭上了改革的“快车”一路高歌猛进,发展势头良好,并在与“作家场”、“期刊场”的抵御与共谋中进一步稳固自己“象征资本颁发者”与“文学史准入权”把控者的地位。
然而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其所带来的结果也并非都是有益的。随着“学院批评”的兴盛,一系列问题也迅速浮现。一方面,在学院批评的体制化、专业化要求下,“考据”、学术规范、客观科学论断以及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定逐渐生长变化为“枷锁”,在赵勇看来,这样的文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成为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过多“黑话”的产生也加剧了批评甚至当代文学的圈子化,种种人为“路障”令批评在与社会现实“绝缘”的路径上一骑绝尘。另一方面,教师职务聘任制度、职务评审制度以及课题申报制度相继建立,最终将原本作为“避世”的“象牙塔”层层分级,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挂钩,进一步加剧高校内部原有的问题。总的来说,“学院批评”既然意图栖身高校,就必然无法摆脱高校自身变动带来的影响,亦无法规避高校改革操盘手的影响,在九十年代,这个隐蔽于阴影之中的“无形之手”则属于政治。
在制度史研究者看来,在整个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和附属物”,“政府对高校教师聘任制度的强控制导致教师聘任制度变迁始终被政府权力左右”,前者通过“编制管理、评审授权、聘任程序、评审条件甚至工资总额控制着高校教师岗位及岗位结构、工作程序甚至高级别岗位的设置条件、收入水平等”。[6]对世纪末的“批评场”而言,这种控制最突出地体现在课题申报制度中。赵勇指出,“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龙头,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项目铺天盖地,它们构成了学院批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动力。”而作为项目的出资方,政府、高校制定了严格的课题申报条件,“以便一开始就对申报者做出某种规范”,为达成申报条件,“申报者之前首先会自我审查”,在课题进行的过程中还有“相关部门的中期检查和‘结项’制度”,这成为规约研究的思想内容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课题、项目数目被人为地与“个人的职称晋升、评奖、收入、待遇和单位的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等等的申报与评估联系在一起”,最终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牵扯多方利益的学术体制。[7]正是在这个层层审查的过程中,文学史的建构权力悄然被挪移到“政治场”中,尽管批评家仍旧把持最终的书写权,但只有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学院批评家”才能成为最终的执笔者,而被“政治场”筛选出来的批评家也同时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从而成为文学的“判官”。在此过程中,属于权力的逻辑清晰可见。当时身处高校且与韩东、朱文齐名的鲁羊对此深有感触:“比如说高校的文学教育,事实上就是一个名利场。具体跟文学本身没有关系,跟判断文学本身的优劣也没有关系,跟文学的起源几乎都没有关系。他的价值所在和名利场差不多。文学是遭遗弃的,在文学研究者眼里,文学是遭遗弃,要研究的是他们对于文学的意向,在互相交换一种意向,而真正他们本应明示,本应彻底比学校外面的人更深地去理解,更透彻地去了解地东西,他们恰恰是很少花力气在上面。”[8]就连一向温和的张生也在后来的访谈中表示研究者对自己这代作家存在某种误解[9]。
可以说,在学院中,“政治场”非但没有像倡导返归“象牙塔”的批评家们所料想的那样消隐,反而更加强力地干涉着这个看似“自主”的文学空间,最终,它也成为现有文学体制的一部分,成为造成世纪末以“断裂”为首的由作家发起的一系列文学行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场”在“政治场”的影响下与“作家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割裂。而若是没有“断裂”事件,“后先锋”也就不会产生,这种割裂也在后者这里得到了延续。参照“后先锋”参与者们的创作谈,不难发现他们与“后先锋批评家”之间也未能完全达成共识:尽管他们都强调建立一个新的“限制性生产次场”,但在此之外,他们也有着属于各自的不同利益诉求。这一现实再度显示出世纪末文学图景的驳杂繁复。
引文:
[1] 王宁:《论学院派批评》,《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
[2]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9页。
[3] 南帆:《90年代的“学院派”批评》,《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第68页。
[4] 赵勇:《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页。
[5] 杨毅:《新中国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变迁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51页。
[6] 杨毅:《新中国高校教师聘任制度变迁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60页。
[7] 赵勇:《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困境》,《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4页。
[8] 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73页。
[9] “包括郜老师,元宝也有一个错觉,他老以为我们这批人,看了80年代那些先锋作家小说去写作的,其实都是错误的。80年代那批先锋作家,他们看的东西和我们看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这批人,当时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欧美高。这样说吧,因为当时苏童啊,马原啊都和韩东很熟,熟了以后,像黑格尔貌的‘仆人眼里无伟人。’所以说没什么神秘的,他们也在看博尔赫斯,为什么我们要去看他们的东西呢?其实我们这批人,看同辈人和国外作家的东西,远远超过看先锋作家的东西。我绝对这是一个很多人的错误的判断。”参加张生访谈,李小杰:《九十年代南京青年作家群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