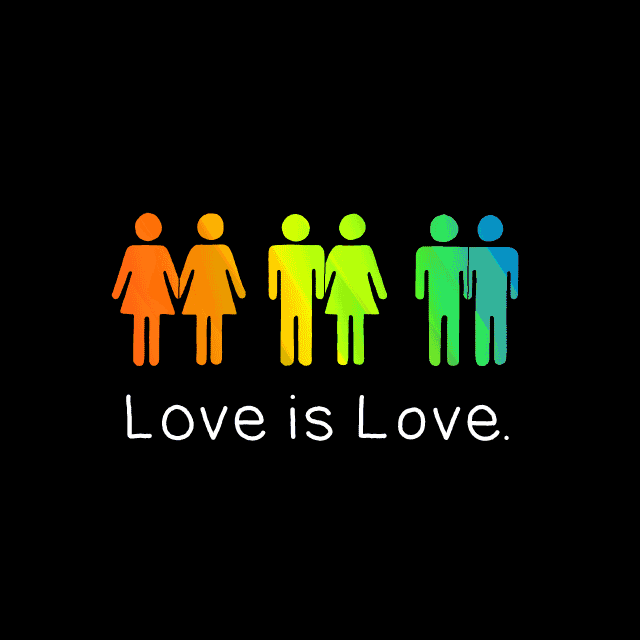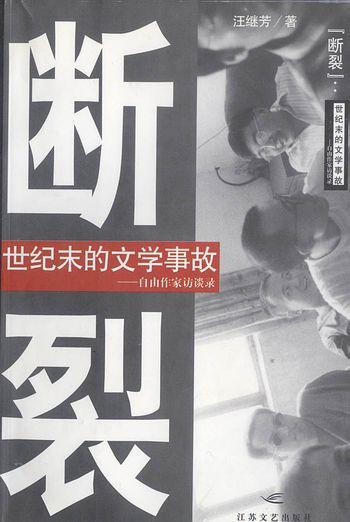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掩饰》摘录
代译序(郭晓飞)
关于骗婚
在中国语境下,在同性恋“骗婚”的话语中,体现了主流对同性恋“冒充”和“坦白”的双重捆绑。
一方面,主流逼着所有人都进入和异性结合的婚姻体制中,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变态、有病、不正常,这催生了冒充的现象;而一旦婚姻中所谓“正常的一方”指控配偶隐瞒同性恋身份骗婚,要求骗子承担法律责任,主流又会纷纷谴责同性恋伤天害理,毁人一世幸福。
制度上,一男一女的婚姻垄断了生育,所以大量的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生育后代,是在预防老无所依,说严重些,那几乎就是求生需求,而不仅仅是为了躲避同性恋的污名。
在谴责同性恋“骗婚”的舆论里,我们很少听到对“强制性异性恋”的批判。好像人们在婚姻问题上已经有了自主性,没有人拿刀架在脖子上让你和异性结婚,然而正如“强制性异性恋”里的“强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强制,“骗婚”里的“骗”也不应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骗,实在值得深长思之。(按:在下意识反驳之前,不如仔细、好好、认真想想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拿刀架在脖子上”。)
关于掩饰
每个人都在掩饰。掩饰,即淡化一个不受欢迎的身份,去迎合主流。在一个日渐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主流的一面,然而被视作“主流”往往还是社会生活的一件必需品。正因如此,本书的每个读者都在有意无意地掩饰着,有时还会为此付出巨大牺牲。
我怀疑他们(按:掩饰的人)都在向一种不公平的现实屈服,这个现实要求他们抑制自己饱受污名的身份,以便生存下去。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污名》:“尽管有的人愿意承认自己具有某种污名……但他们会极力阻止污点被放大。”这种行为即是“掩饰”。它与冒充的区别在于,冒充是关于一个特定属性的“可见性”,而掩饰则是关于它的**“耀眼性”**。
我讨厌的是我需要压抑我对同性恋话题、人群、文化的激情——好像这些仍然是我应该感到羞耻的兴趣一样。
我们正处于美国人转变歧视方式的时代。对于老一辈而言,歧视是针对一整类人的——对少数族裔、女人、同性恋、少数教派或残疾人施加限制。在新的时代,歧视不再指向一整个群体,而是针对这些群体里不服从于主流规范的拿一部分人。这种新形式的歧视瞄准的不是少数人群,而是边缘文化。局外人也可以被接纳,但前提条件是我们得像个局内人——换言之,只要我们能掩饰。
这是个进步:人们不再需要成为白人、男人、异性恋、新教徒和健全人;他们只需要装得像白人、男人、异性恋、新教徒和健全人。但是这并不是平等。
当代民权只关注传统的民权群体,如少数族裔、女人、同性恋、少数教派及残疾人,这本来就是个错误。因为这就假定在所谓的主流社会中的人——那些异性恋白种男人——就没有掩饰着的自我了。他们就只被当成障碍物,只被当成妨碍其他人自我表现的人。也难怪他们常常对民权倡导报以敌意。他们觉得我们是在要求一种他们得不到的权利——对人性的充分表达。
民权的升华始于承认主流社会只是个神话。正如酷儿理论家们洞见的那样,完全正常就是种不正常。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表达;我们每个人都有掩藏着的自我。
关于同性恋的矫正
矫正同性恋的要求在我们的文化里越来越不受待见。社会控制的三架引擎——法律、医学和宗教——都已经开始撤回这一要求。
如今矫正的要求已经变得更加细致,四处弥散,也正因如此,它才变得更难抵抗。我被液体包围,而我在其中游动。我不能想象异性恋之外的生活,就如一条鱼不能想象在陆地上闲逛。
最为强烈的矫正要求是施加在性摇摆者身上的,也就是那些在性上模棱两可或尚未定型的人。
关于禁令
就算人们不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真正的疾病(一种精神疾病),但同性恋是种象征性的疾病(一种不受欢迎的、会传染的习性)这一观念却延续了下来。反同心理学家们已经明确把它命名为“同性恋的传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孩子们一旦跟着同性恋者产生性接触,就会被引导成或沾染上同性恋。”
传染模式的隐喻反映了社会对同性恋根深蒂固的恐惧——同性恋者会把症状传给他人——这种恐惧比真正的精神病模式荼毒更深。同性恋被当成如此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为禁止宣传同性恋的政策提供了合理性,因为这样的禁令看上去只是在被动防守。
然而,同性恋宣传禁令本身的攻击性却被遮蔽了,就像改名为“国防部”的政府部门掩盖了其发动战争的本事。因为如果孩子们坦言自己性倾向游移,那么同性恋宣传禁令就跟哪些试图把他们转变为异性恋的手段没什么两样。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法律认可了传染模式,它们就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理直气壮地把同性恋视为一种病。
不可改变论
近些年,我看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人们对同性恋的维护并不是基于它是“好的”,而是基于它是“不可改变”的。
拿不可改变为同性恋来辩护并不是最佳方案,因为它隐含着一种歉疚感。它在拒绝矫正的要求时只是说“我没办法改变”,而不是说“我不愿意改变”。它似乎在说,电击疗法是错误的,仅仅是因为它没有效果;而如果它有效的话,它就没有任何错误。
正如乔纳森·托林斯的话剧《神界的黄昏》所设想的那样,从发现一个同性恋基因到观察到一个带着这种基因的胎儿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科学家们赶在同性恋者改变偏见文化、保障合法权益之前发现了一个同性恋基因,那么届时的同性恋者会比我们今天的处境危险得多。
正文
关于同性恋的冒充
冒充这一规范不仅是仗着同性恋的沉默,而且是倚赖反同者对这种沉默的坚持才建立起来的。
关于出柜
没有什么比最初几次的出柜经历更能让我相信语言的力量了——话音一落,你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对于很多男同性恋而言,出柜是最接近于生孩子的事情了。把自己生出来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令人害怕的,绝不可能做到平静。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欣喜是幼稚的。我根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出柜,因为每个我新认识的人都在我周围立起了一个新的柜子。更为微妙的是,就算那些知道我是同性恋的人们也在强加给我一些新的要求,要我服从于异性恋。
当一个人冒充成异性恋时,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柜子。这使得出柜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都成了一场西西弗斯式的事业。
即使我刚刚讲述的故事比我之前讲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完整,但它们还是充满了简化与回避。或许这就是那个水手的窘境(按:指《古舟子咏》中的水手)——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从某些故事里跳出来,即使我们看见自己被困在里面。(按:语言之力的悖谬)
本应该彻底推翻旧政策的法院如今却接受了新政策,只因后者被包装成了一个“进步”的故事:曾几何时同性恋者还得接受治疗,而在如今这个更文明的时代,他们只需要冒充一下异性恋而已嘛。
如果我们有成为某种人的权利,那么我相信,从逻辑上和道德上来讲,一定就会有说出自己是什么人的权利。当军队说自己并不是反对同性恋,而只是反对公开的同性恋时,我觉得这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使我对前半句话都存疑万分。
关于同性恋的掩饰
世纪之交,同化对同性恋的要求开始从矫正变为冒充再变为掩饰。如今,在美国的许多行业,我们都可以做同性恋,也可以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只要我们别“张扬”。
麦克·沃纳:“当那些由各种规范所定义的人们开始用‘正常’这一标尺来衡量自己的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价值时,他们就是在进行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自杀。”酷儿们应该“坚持让主流文化向酷儿文化靠拢,而不是相反”(按:如果你认为自己属于二次元群体的话,稍微带入一下就能理解了)。
同性恋群体内部的分化
随着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逐渐温和,过去“好”异性恋和“坏”同性恋之间的界限在某些情境下发生了变化。如今“好”异性恋和正常的同性恋站在了一边,而另一边是“坏”酷儿。**同性恋不再是一个笼而统之的病态群体,许多人越来越迫切地觉得,有必要站到某个队伍里以表忠心——他们要么充满感激地融入主流社会,要么以捍卫差异之名抗争到底。**非裔美国人在融合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争论不休,女性分裂为平等女权主义和差异女权主义,同样地,同性恋群体也在“好同志”和酷儿之间产生了分歧。
好同志责骂酷儿,因为他们觉得酷儿让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染上了坏名声。这些耀眼的离群者“让人产生很多误解,从而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
酷儿也会攻击好同志,因为他们觉得那种想要变得正常从而被异性恋社会接受的做法是一种背叛。沃纳批评好同志,说他们“羞辱着那些站在体面阶梯最底层的人”。
掩饰的四个方面
外表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向世界展示她的身体;归属涉及她的文化认同;社会运动关系到她在何种程度上将她的身份政治化;而人际关系则有关她对同伴的选择——包括爱人、朋友、同事。
在这四个最基本的维度上,我们所有人都在隐藏或炫耀我们的身份。
外表:
可以说,同性恋权利诉讼和公共关系维持都受同一动力驱使,即,希望把同性恋者打造成除了性倾向之外,在所有方面都跟异性恋别无二致的人,好像在做一个控制变量的实验。
讽刺的是“扮直人”的冲动最初来源于同性恋者自身。(如戈夫曼所言,被污名化的群体常常强烈地希望自己“正常化”)。
归属:
在这种文化场域中(按:书中是一个同性恋社区,你也可以理解为gay bar),他可以想象同性恋平权,他正常的欲望不会被当作变态。在这里,他可以挽回时间,重新体验他从未有过的青春,与朋友共享欢乐,而不用因为一个可怕的秘密就跟他们疏远。
在火车上不知坐了多久,我抬起头,突然察觉到某个时刻已经到来了——异性恋文化重申了它的霸权。那些蜷缩在对方怀里的男人们在这一刻分开了,紧扣的食指瞬间松掉,满是刺青的身体已经消失在外套中,一张张面孔紧绷起来。这个时刻是如此细微而难以察觉,就像季节的更替,或是一个人突然就没了爱情。(按:这种地下情人式的感受或许在封控时期的校内校外爱情中有所表现,但要知道后者只不过是一种极端情况而前者往往是常态,如此一来,换位思考一下或许就不那么难理解了吧。)
人际关系:
福柯:“人们可以宽容两个同性恋者在他们面前一同离去,但如果第二天他们微笑着,牵着手,温柔地拥抱着对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常常被描述成不稳定的、孤立的、滥交的。这一形象意味着,如果同性恋者更加自重,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多尊重。如果同性恋之间有爱,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爱。
如果同性恋者把恋情保持在地下,道德卫士则仍然可以把我们的感情当作废弃品。然而最令他们焦躁的是一对同性恋人向他们证明,这段感情很成功,而且两人都很快乐。(按:懂还得是福柯懂。)
掩饰在道德上也很复杂。
很多人都同意矫正和冒充会造成巨大伤害,却觉得掩饰无伤大雅。对于那些反对冒充却支持掩饰的人,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他们的立场站不住脚,因为冒充和掩饰常常难以区分。同样的行为——比如拒绝牵同性的受——既可以是冒充异性恋,也可以是掩饰同性恋,取决于观众是否知情。
更深层次的、更加发自肺腑的回答是:我有了身为同性恋的权利,也有说出自己是同性恋的权利,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的生命经验也告诉我,它们是微乎其微的。对我而言,只有当我克服了掩饰的要求时,同性恋才能从一种状态变成一种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拥有我的感情,我的文化,我的政治,我的爱人。只有这样,同性恋的生命里才能有一丝快乐。
重要的是我拥有在所有维度发现或展示我身份的自由,且不被偏见所束缚。
那些致力于同性恋平权的人不能只问,某种行为是否是“成为同性恋”所必需的。很多东西同性恋者就算没有也能过活,包括平等。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同样的行为是不是由异性恋者做出来就可以接受,同性恋者就不行。
掩饰的要求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它直指不平等的心脏地带——它让一类人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就是比其他人更高级。当异性恋要求同性恋掩饰时,他们是在要求我们变得渺小,要求我们放弃异性恋所拥有的权利,最终放弃平等。如果法院只有在同性恋者掩饰自己的前提下才肯保障他们的重要权利——如就业权或监护权,那么法院就是在合理合法地把同性恋者变成二等公民。
正因如此,比起那些说自己支持同性平权却又希望同性恋者掩饰起来的人,我在智识上反而更加尊重那些说自己反对同性平权并且希望他们矫正成异性恋的人。憎恨同性恋并要求所有形式的同化,在逻辑上至少是一致的,而一边支持平权一边又敦促同性恋通过掩饰变成二等公民,才是自相矛盾。
种族掩饰
一个可悲的事实时,对于种族主义而言,最有效的心灵解药正是种族主义本身。我在一个国家遇到的种族主义观念都会在另一个国家有镜像般的呈现。
法律往往关注的是少数群体是否能够按照主流群体的标准改变,而完全不过问后者为什么会要求这样的同化。如果真要检验后者的理由,它们往往都是站不住脚的。
性别掩饰
对女性的掩饰的两种要求往往同时存在:掩饰和逆向掩饰。许多命令并不是要所有人都服从,而是专门针对女性的。
如果说同性恋者或少数族裔也会卷入掩饰和逆向掩饰的交火之中,那多半是因为我们身陷两个群体。多数派阵营(异性恋者或白人)提出掩饰 要求,而少数派团体(同性恋者或少数族裔)则提出逆向掩饰的要求。相比之下,女性更为特殊,因为强势群体——男性——通常会既要求她们掩饰,又要求她们逆向掩饰。
在工作场所,女性必须有足够的“男子气”才能被视为值得尊重的职场人士,但她们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女人味”才能被视为值得尊重的女人。
这些精神分裂式的要求造就了一个经典的双重捆绑。在研究女性律师时,罗德指出:“职场妈妈常常被批评为不够投入,既当不好父母,也当不好专业人士。”“这些混杂的信号让女人不安,因为不管她们在做什么,总有人觉得她们本应该做别的事。”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两个要求(掩饰和逆向掩饰)没有办法同时满足,而是在于没有任何一个要求是理所当然必须满足的。
出路设想
进步律师大多会认为照顾原则就是法律上的青霉素。他们希望把这一原则从宗教和残疾扩大到种族、性别和性倾向。
联邦最高法院曾明确以身份爆炸为由,为其保护不力作辩解。坚持同案同判意味着,如果最高法院保护某一个群体的行为,那么它必须保护所有类似群体的行为。法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时干脆完全不保护任何行为,只保障身份中那些不可改变的因素。(滑坡理论)
布伦南对这一滑坡理论给予了冷嘲热讽的回应,称它似乎是在**“担心有太多公平”。这句话显示了一种社会病态,即大量的社会不公反而成了保持现状的借口**。
比起一小群人追求的“平等”,法院对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自由”更为关注。原因很简单:有关平等的诉求——比如基于少数群体的照顾原则——不免会让最高法院在众多群体中选出几个最爱。在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法院根本不想搅这趟混水。相反,有关自由的诉求则会强调所有人的共通之处。
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那些行为举止很“主流”的人一定就是在掩饰。我们最终要追求的是自主,并将自主视作实现真实性的一种途径,而不是追求一个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固定概念。
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我们所有的公民,而不是公民中的一小部分律师。那些不是律师的人应该在法律之外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应该把戈夫曼的“掩饰”一词从学术的晦涩中抽取出来,把它装进通俗词库里,从而使它变得跟“冒充”或“出柜”一样普及。而那些遭遇掩饰要求的人们则应该大胆质疑这些要求的合理性,即使法律尚未约束那些提出要求的人,也尚未认可那些被要求的群体。
译后记(朱静姝)
关于同妻
同妻在婚姻中的痛苦无可否认,但《掩饰》却提醒我们反思,首先是什么样的社会同化机制把同性恋者逼进婚姻里——要知道,同性恋者从来没有机会不冒充、不掩饰、名正言顺地跟自己喜爱的人去过有法律保障的生活,而异性恋者不仅“理所当然”地拥有结婚的权力,还在主流性道德里占据着上风。
**同妻们也是同化的对象,她们只有在成功扮演了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勤俭持家、温婉贤淑、守身如玉之后,才有资格谴责同性恋丈夫的“背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看不到那些勇敢突破束缚、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与性的同妻,而只能在媒体上看到悲惨的同妻故事,千篇一律地讲述着性向不合的婚姻如何剥夺了好女人的毕生幸福。毕竟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情欲自主”仍然不被主流道德接纳,是一件就算可以做,也最好不要张扬的事情。可见,掩饰背后的性污名既捆绑着同志,也束缚着同妻。(按:洞见)
遗憾的是,不少同性恋者身为被主流性道德排挤的人,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掩饰的要求转移到更加被污名化的群体身上。
没有人时刻都活在宇宙中心,我们总有不符合社会期待、需要无奈掩饰的时刻。脆弱从来都不只是少数群体的特质,脆弱属于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