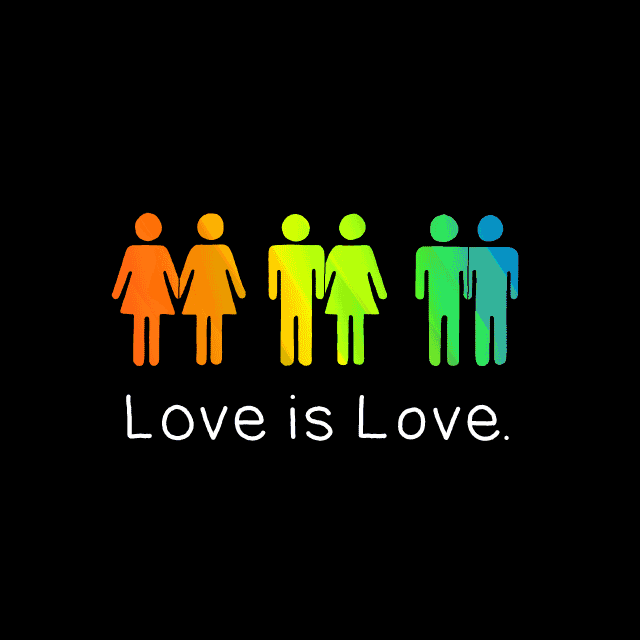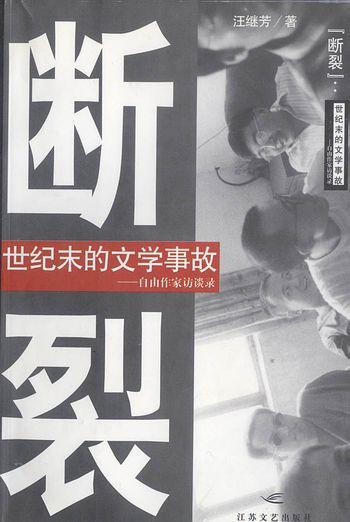《繁花》读后兼与《长恨歌》简单对读
阿宝、沪生、小毛作为三个锚点,在作家笔下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上海帮我们衔接起流动变迁的时间和发生在各个时间节点上的事件。这串联衔接的过程又像饱经风霜的老者拿一把钥匙开启被锈迹斑斑的锁封存的屋子,漫不经心地在遍布尘埃的老旧屋子的角落中寻回一块块干燥少色的拼图,然后蹲坐着,戴上廉价的老花镜,眯缝着眼睛,一块块将它们对着从帘幕中透出的晌午的光,用纤巧的刷子打理干净,在手里摩挲半晌才不舍地拼接起来。因此,越读到后面,那副原本模糊了的图像就愈发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原本随着时间逝去了的那些发生在过往事件上的悲哀和怅惘也就随此一点点积聚起来,漫延、晕染,就像一拳一拳冲击着屏障同一个地方,最终击碎原本就存在的裂隙的部分,令人难过得红了眼圈,淌下些泪来。但这悲伤既不像张爱玲刻骨的凉意,看透世事冷眼中散发的寒冷与时代、世情带给人的特有的疲倦感(当然背后更有隐微的余热——被水浇灭的柴薪中最后的几乎看不见的余热),又不像王安忆为往事披挂一层泛黄滤镜继而在旁一点点摄录呈现,通过零零碎碎的时光与杂陈琐屑的物件抖露些被人、事、物所负的凄然。它就只是从一点点流逝的时光中积累起来的一层层哀感的综合,经由一次不经心的回望得以被点燃,最终留下深入却又淡淡的怅惘(因积累和时间的叠层而深刻,又因此而淡然)。
促成这份悲伤的另一因素是语言和故事的讲述方式。俗白浅近的上海口语以接近古文的短促句子密集地向读者排闼而来,不仅令人感到活色生香,更使人觉得新异。以对话的形式构建的叙述方式天然同口语契合,又同时在描摹的地方换用更雅的文言:评弹讲唱辞令、古今中外诗句歌词、大量专有名词,将整体从俗拉回,语言整体的平衡性得到保证,也构成现当代文学中独有又不可复制的语言模式(借用敬老师对《围城》的评价:这样的写作具有唯一性,不仅是其它作者不可复制的,就连金宇澄本人也无法复制)。
十里洋场的人事在细碎的时光隧道里沟通了不同的写作路径。九十年代灯红酒绿的宴请与欲海恰若穆时英与刘呐鸥笔下跳着狐步舞、站在高楼边抽雪茄边望着夜幕的密斯特和密斯们,都是醉生梦死却又脆弱易碎的。在他们这里,名利携欲望作了霓虹的光,在觥筹交错的酒杯,闪烁夺目的珠宝中流动,既慑人心魄令人向往,又透照出皮相下血肉里庸俗无聊的人性(汪小姐与徐总,梅瑞与康总,李李与阿宝,小琴与陶陶,无一例外跌得惨重)。市场迷梦之前的那些岁月又学了新写实和王朔的骨法(浅俗油滑自有市民社会的味道,但在当代终归是从王朔开始大规模复兴的;而新写实的抽离细碎本质上还是福楼拜的一脉),游离在历史的边缘,不主动避开也不直白地冲上去与之短兵相接。与其类似的疏离同样出现在《长恨歌》中,只是由于叙述语调、视角以及方式的差异,王安忆笔下的这段时光始终有着物是人非的戚然,无论是情绪的表露还是内容的叙写上都向内收紧,即便是写程先生自缢的一段也还是那样掰开了揉碎了的样态,似乎说的只是一件“故事”,由之表露的沉痛也是透过人物如今与以往堆叠起的遭际和心境、言语才得以呈现的,像是伴着晚钟震响而振起翻飞之乌的啼鸣。《繁花》则更为坦然,几乎就不流露出情绪的意味(但这是不可能不存在的),生活就如其自然地铺展着自己的样子,人也随着生活扬起的流波恣意向前涌着。相较之下,金宇澄倒是更得自然主义真传,其对传统的所取也更多源于《金瓶梅》而非《红楼梦》。从人性表露的角度看,《繁花》对这段时间的描写更注重人平日里涌现的欲望与欲望的满足,《长恨歌》则更注重人性、欲望的压抑与摧残。说到这里,也就看得出这部书也还是逃不出人的欲望与苦难这两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母题。
由始至终,金宇澄对于欲望的呈现紧扣性不放。因着语言的浅白和时代铸就身处其中人的卑琐,人与人的性需要都显得世俗、丑陋,甚至有些“下作”:5室阿姨的“放荡”、二楼爷叔的窥淫、九十年代中层出不穷的劈腿、富于性暗示的装扮和目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物那里的性书写及其背后的意义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
酷烈时代中的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唤回人性的价值,言说上的羞赧与实际行动中的热烈构成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张力,它实际是在群体要求个体自我泯灭的时代中个体的生命赞歌。因此银凤和小毛的性并不让人觉得卑劣,更不会引人唾弃;姝华在面对掉落在地的生理书时所表露出的自然和随后而来的羞赧也更多让人打心底里觉得她的可爱;就是黄毛与5室阿姨在车间略显放肆的欢情也能让人感到同情。
在这个时代,反倒是失了语的性成为了一种残酷的压迫。远赴东北的姝华一路回到上海,早已不复曾经浸润在书香中的灵气,接连不断的生育令她几近精神失常;二楼爷叔无声的窥探、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海德希望让外人拍摄银凤的照片、一声不响中对小毛银凤之间情感的破坏(在这里不对道德问题进行探讨),都是在无声中对人性中美好存在的有意无意的毁坏,既显示出施害者自身的心理残疾,又显示出他们对被害者的残酷。
饶有意味的是,九十年代的情况正好与此颠倒。被大书特书的性与欲望反倒更多成为追求它们的人的禁锢,反倒是那些含而不露的性蕴匿着源于心底的真情。
汪小姐与徐总的孽缘、陶陶与潘静小琴的欢爱,康总和梅瑞的暧昧,情欲流溢在时代的弦音里,几乎构成生活之声的一个主题;相反,游离于所有女性之间的阿宝和沪生,最终离开人世的小毛,却都是看似离欲望最近但实际上却隔得最远的人。这也真应了汪小姐那句话“这个社会,文雅面孔的人,生活往往一塌糊涂,看上去花头十足的,比如宝总,也许是老实人。”在周宝欣看来这样一种畸形状态源于“长久的物质匾乏和历史性的礼教、政治社会对欲望、本能、日常要求的道德乌托邦钳制,使多数民众在经济社会迅速形成一种现代性时尚的自我补偿心理。”(见《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
稍微把话说开去一点,笔者在这里的解释可以上升为对当代文学绕不开性书写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而这种将性作为人的生命力量的表征的观念也不过是叔本华、尼采一脉的现代西方哲学早已阐述得不能再确切的一种看法。虽然就我的阅读和知识水平难以提供一个更为新近合理的性的理解,至少,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不宜轻易对当代文学中的过度存在的性描写抱有那么大的怨恨(当然,也同样不宜对所有性描写都全盘接收)(我也不知写这句话到底有没有意义,一般来说关注我的人应该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想了想还是觉得加上吧)。
说罢欲望,接下来探讨另一个核心——苦难。
读当代作品我总是忍不住想苦中作乐真不愧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良好美德,以至于作家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写了又写,你写我写大家写,最终把写作这件事本身也变为苦中作乐的一环。由苦中作乐很容易引申出中国人另一个源远流长的良好美德——坚韧,在这里,远在欧陆中心的思想又一次在东方饱经摧残的土地上翻出新芽,茁壮成长,如果加缪萨特多在中国待些时日,多看些底层人的生活,想必存在哲学会被完善得,也写得更好。但我总觉得这不争与忍受的美德实在是太泛滥了些以至于让人觉得倒胃。况且这也不是事情的全部,正如鲁迅洞察的那样,人们往往在忍耐上层加诸于身的苦难的同时又尽了情任了性地对更底层更弱势的人残忍、剥削。阿宝爸爸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在遭际上可谓是受尽了苦难与折磨,但面对阿宝却也还是如此绝情,禁止他与香港的哥哥通信,甚至跟踪调查自己儿子的一举一动;二楼爷叔猥琐,淫欲不能得到满足,最终亲自破坏银风和小毛的感情。不过,在遍布禁忌和压迫的生活中向更弱势者抽刃,只是《繁花》苦难书写中的一部分。作为主题的苦难实际还是透过发生在个体身上层层堆叠的事件以及最后造成的那种物是人非得以展现的。在这一点上,《长恨歌》与之十分相似中又有所区别。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苦难很少被直接展露,在每一个时代的切片中,她的生活一直维持着最基本的体面,即便是在最残酷的时代里她也小心翼翼地躲闪过去,因此她的不变实际上成为王安忆在写作中最为重视的内容。在书里(除了尾声部分),她一直是作为时代的见证人的身份存在的:她身边人物的来和去其实就意味着时代的前行,而她自己在整个过程中“容颜永驻”,无论何时都显得那么年轻。某种程度上,王琦瑶的不变恒定与她周围人物的流动不息正是苦难得以刻印的方式,那种愈发浓厚的物是人非之感一点点随着时代的行进加剧,尤其当与她关系密切的男性一个个离开又亡逝,前朝遗老式的悲慨一次又一次被提起,直到最后,她本人就成为了一个凝定了的故往时代的印记。
《繁花》则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苦难带来的悲感在人物的不复往昔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呈现。阿宝爸爸口中欧阳老师被释放平反后的样态与黎老师在饱经苦难的几十年后对陌生小囡阿宝的倾诉,鲜活地道出时间(以及在这些时间中发生的其它因素——这里最令人感慨的是那句“天又要亮了,不是微亮,马上大放光明了,光明世界,马上就要到了”)的残忍。而经过一个个事件/时间碎片的堆叠,当阿宝、小毛、沪生三人的形象终于以一个整全的样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却深深感到他们不再如初(尤其与小毛重逢一段,道出人世多少类同的悲欢),正是这年少与成熟之间的区隔令人看到时间的巨力。
这里其实存在一个所谓的从“时间”到“苦难”的转换:在这里的论述似乎围着时间,实际却还是绕不过苦难。如果仅仅是时间带来的变动,物是人非的感受原不可能如书里传递、读者所接受到的这么深重,正是基于时间的变换所带来的社会、家庭、身边人的变动才使得个体的变动显得无比沉痛。以阿宝为例,自始至终未作变动的叙述口吻给人一种他被凝定的错觉,实际上在一件件与他或有直接关联或无直接关联的事情后,他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小囡。与蓓蒂和阿婆回乡,父亲被打倒全家被迫搬迁,蓓蒂与阿婆失踪,与雪芝的感情被两家人拆散,亲自听到黎老师讲述自己一生,与小毛绝交时隔十多年后再相识,与李李的感情,亲自送走故友小毛,在十里洋场耳濡目染,每一件徜徉于时代潮汐中的事项都对阿宝自己人格的塑造产生了影响。他在很多场合里的“不响”实际也正表露出他对世态人情的看法。当然,更典型的是小毛,相较于阿宝的含糊,小毛的一生转折更为明确,他与银凤的生别离,与阿宝、沪生的绝交,春香的惨死,以至于最后自己的病重,无一不显示出“苦难”对个体的摧残。
尽管金宇澄自诩承续自然主义,书中对于酷烈时代的惨痛与残酷的描绘还是让“苦难”的面目得到展现。我想他的不回避其实是在提示读者不要再去回避,也在提示研究者不要再回避,显然,即便十年之后,如今的我们对此做得还不够多。这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仍需要这样的小说,仍需不断阅读它们,作家仍需对历史不断复写的原因。